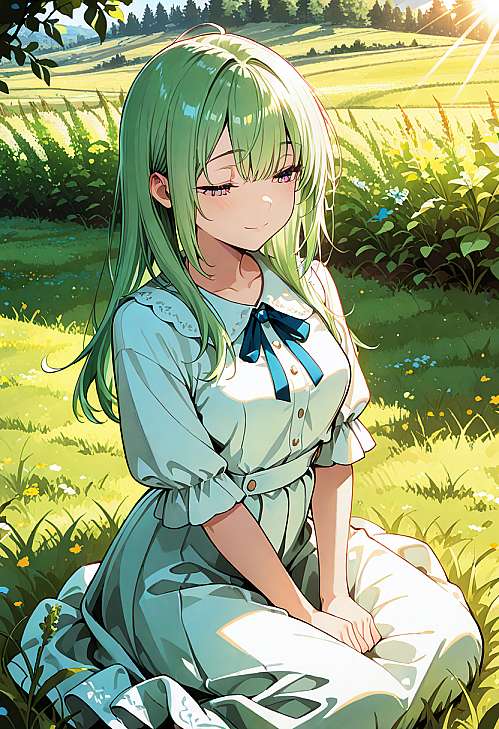第一章黑暗。无边无际的黑暗,混着陈腐的木屑气息,死死堵住江澜因的口鼻。
她猛地睁开眼。什么都看不见。头顶是低矮的木板,紧紧贴着鼻尖,
每一次呼吸都带起细碎的木屑,呛进喉咙里,引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。
可咳嗽声也被闷在咫尺之间的空间里,震得耳膜嗡嗡作响。这是哪儿?她下意识伸手去推,
指尖触到的是粗糙的松木板,冰凉,坚硬,纹丝不动。掌心传来一阵刺痛——指甲劈裂了,
血肉模糊,可她根本记不清这伤是什么时候留下的。记忆像破碎的瓷片,
在脑子里混乱地翻涌。甘露寺的十年,青灯古佛,晨钟暮鼓。她跪在蒲团上,
一遍遍抄写经文,为“殉情”的表妹祈福。右手腕上空空荡荡,
断口处每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——那只手,被皇后娘娘下令斩落,封进了太子的衣冠冢。
她忍了。爹说,是她懦弱害死了表妹,她该还。娘说,表妹还是个孩子,死得为何不是她。
大哥说,她只是失去一只手,表妹可是没了命。她都忍了。可最后呢?十年后,
太子活着回来了。表妹也活着回来了。他们携手走过大江南北,看尽江南烟雨、大漠孤烟,
还生了三个孩子。而她这个在甘露寺苦守十年的“太子妃”,像个笑话。更可笑的是,
表妹要当皇后,所以她这个“前太子妃”必须死。“因因,你忍一忍,再忍一忍,
这辈子就过去了。”这是她临死前,亲耳听到的最后一句话。是爹的声音。
她记得那碗药灌进喉咙时的灼痛,记得五脏六腑像被人生生撕裂的滋味,
记得咽气前最后看到的——是大哥站在床前,面无表情地看着她咽气。她死了。
那现在这是哪儿?“咣——”头顶传来沉闷的声响,像是有人在钉什么东西。
钉子穿透木板的声音,尖锐刺耳,一下一下,震得她头皮发麻。钉棺材。
江澜因浑身血液瞬间冻结。她想起来了。太子“战死”的第七天,皇后下懿旨,
让她与太子结冥婚。爹娘逼她穿上嫁衣,大哥亲手把她塞进棺材——就像现在这样。上辈子,
她在棺材里躺了三天三夜,哭干了眼泪,喊哑了嗓子,最后被人从棺材里拖出来,
押到皇后面前,砍断了一只手。那是她噩梦的开始。可上辈子,她被塞进棺材时是昏迷的。
为什么这辈子,她是醒着的?“动作快些,吉时就要到了。”棺材外传来男人不耐烦的声音。
江澜因瞳孔骤缩。江慎——她的大哥。那个上辈子按着她让皇后砍手的大哥,
那个看着她咽气时面无表情的大哥,那个从小到大,曾几何时也曾疼过她的大哥。“世子,
这棺材钉得太紧,回头皇后娘娘要是还想……”有人迟疑。“想什么想?”江慎打断他,
“她这种懦弱无能、害死表妹的东西,能配给太子冥婚,已经是天大的福分。
皇后娘娘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法?”话音落地,又是一阵沉闷的敲击声。
棺材盖在头顶一寸一寸合拢,光线越来越暗,空气越来越稀薄。江澜因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
疼。可这疼,跟上辈子被灌下毒药时的疼比起来,算得了什么?
跟被活活斩断一只手时的疼比起来,算得了什么?
跟十年青灯古佛、最后等来一个笑话的疼比起来,算得了什么?她活过来了。
老天爷让她带着上辈子的记忆,在这棺材里活过来了。棺材盖合拢前的最后一缕光线,
照在她脸上。江澜因忽然笑了。笑容很轻,很淡,却带着上辈子临死前才淬炼出的冰冷。爹,
娘,大哥,表妹,太子,皇后……一个一个,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上辈子欠她的,这辈子,
该还了。“砰——”最后一颗钉子钉死,棺材里彻底陷入黑暗。空气越来越稀薄,
胸腔像要炸开一样。江澜因躺在那儿,一动不动,静静感受着窒息带来的眩晕。上辈子,
她也是这样躺着,哭着,求着,盼着有人能来救她。结果呢?没有人来。这辈子,她不求了。
指甲劈裂的指尖摸索着,触到身下铺着的白色丝缎——那是冥婚用的“喜被”,白得刺目,
白得像灵堂里的孝布。她咬破指尖。血珠渗出来,在黑暗中看不见,
却能感觉到温热的液体顺着指缝流淌。她在身下的白缎上,一笔一划地写。写得太子的名字,
表妹的名字,爹娘的名字,大哥的名字。写她上辈子受的十年苦,
写她临死前听到的那句“再忍一忍”。最后,她写下八个字:“江澜因在此,拜谢诸位。
”指尖的血已经凝固,她再次咬破,继续写。不是遗书,是账本。上辈子的账,她一笔一笔,
全都记下了。棺材外的声音渐渐远去,脚步声、说话声,都听不见了。只剩下无边的寂静,
和越来越微弱的呼吸。江澜因闭上眼睛。她不知道这次能在棺材里躺多久,但她知道,
只要她还活着,只要她从这棺材里爬出去——那些人,一个都跑不掉。恍惚间,
上辈子的记忆像潮水般涌来。甘露寺的十年,她是怎么熬过来的?每天清晨四点起床,扫地,
挑水,诵经。冬天手生冻疮,烂得露出骨头,还要跪在冰冷的蒲团上抄经文。夏天蚊虫叮咬,
浑身肿得不成样子,还要忍着痒去后山砍柴。她没了一只手,做这些比常人难十倍。
可师父说,这是为她表妹祈福,为她赎罪。她信了。她真的信了。她以为表妹是为她死的,
她以为自己是欠表妹的。所以她心甘情愿受苦,心甘情愿熬着,盼着死后能见到太子,
亲口对他说一声对不起。可结果呢?结果她十年苦修,换来的是太子和表妹双宿双飞的十年。
结果她盼着死后能见的太子,亲自下旨,要把她这个“前太子妃”处死,好给表妹腾位置。
结果她亲爹端着毒药喂到她嘴边,说“因因,你再忍一忍,这辈子就过去了”。她忍了,
然后死了。这辈子,她不忍了。黑暗中的时间过得格外缓慢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
棺材外又响起脚步声。“打开。”是皇后的声音。江澜因猛地睁开眼。上辈子,
皇后可没来开过棺材。她被关足了三天三夜,被人拖出来时已经奄奄一息,根本没力气反抗。
这辈子,怎么才半日就开了?棺材盖被撬开,刺目的光线涌入。江澜因眯起眼,
看见一张张俯视的脸——皇后身边的嬷嬷,东宫的太监,还有……她的大哥,江慎。“出来。
”嬷嬷伸手去拽她。江澜因没有挣扎,任由她们把自己从棺材里拖出来。她浑身无力,
脸色苍白得像纸,嘴唇毫无血色,劈裂的指尖还在渗血,染红了白色的嫁衣。可她站直了。
“皇后娘娘呢?”她问,声音沙哑,却很稳。嬷嬷一愣:“你……”“我问,皇后娘娘呢?
”江澜因看着她,眼神平静得可怕,“不是要结冥婚吗?皇后娘娘不来主婚?
”江慎皱起眉头,上前一步:“江澜因,你发什么疯?”江澜因转过头,
看向这个曾经的大哥。上辈子,他是怎么按着她让皇后砍手的来着?对了,他说:“江澜因,
你只是失去一只手,表妹她可是没了命!”说这话的时候,他脸上没有半分愧疚,
只有理所当然的厌恶。江澜因笑了。笑得江慎心里发毛。“你笑什么?”他警惕地问。
“没什么。”江澜因收回视线,“走吧,去见皇后娘娘。”她提起裙摆,
自己往灵堂的方向走去。身后,江慎和嬷嬷面面相觑。这个江澜因,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?
太子的灵堂设在东宫正殿。满目素白,白绸飘摇,烛火摇曳。正中央是太子的牌位,
前面摆着供品、香炉,还有一对粗如儿臂的白色喜烛——冥婚用的喜烛。皇后何氏坐在一旁,
手持念珠,满脸哀戚。周围站满了前来吊唁的命妇和朝臣——她们都是来看这场“冥婚”的。
江澜因被押进来的时候,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。白色的嫁衣,散乱的长发,
苍白的脸色,还有——指尖滴落的血,一滴一滴,落在汉白玉的地砖上,触目惊心。“跪下!
”嬷嬷按住她的肩膀,要她给皇后行礼。江澜因没有跪。她抬起头,看向皇后。上辈子,
就是这个人,轻飘飘一句话,砍了她一只手。说什么“太子生前最喜欢你这只巧手”,
说什么“舍出一只手陪伴我儿,不过分吧”。不过分?砍别人的手,当然不过分。
江澜因静静地看着她,嘴角慢慢勾起一个弧度。皇后皱起眉头:“江氏,见了本宫,
为何不跪?”“皇后娘娘。”江澜因开口,声音不疾不徐,“臣女有一事不明,想请教娘娘。
”满堂哗然。一个被塞进棺材的准冥婚新娘,竟然敢这样跟皇后说话?江慎脸色大变,
冲上来就要拽她:“江澜因,你疯了!”江澜因侧身避开,看都没看他一眼,只盯着皇后。
皇后的脸色沉下来:“你想问什么?”“臣女想问——”江澜因一字一顿,“表妹文氏,
当真死了吗?”此言一出,满堂寂静。随即,议论声四起。“她说什么?文家姑娘没死?
”“怎么可能,那天多少人都看见她撞柱殉情了!”“血都流了一地,怎么会没死?
”皇后的脸色变了。江慎的脸色也变了。江澜因把他们的反应看在眼里,心底冷笑。上辈子,
她被关在棺材里三天三夜,什么都不知道。等她被拖出来时,
表妹“殉情”的事已经成了定局,所有人都说是她懦弱无能,逼得表妹替她去死。
她连一句辩解的机会都没有。这辈子,她不进棺材,她要亲眼看看,
那场“殉情”到底是怎么演的。“胡说八道!”江慎怒喝,“表妹撞柱殉情,
满京城的百姓都看见了!你、你竟敢在太子灵前胡言乱语,亵渎亡灵!
”他冲上来就要捂江澜因的嘴。江澜因一把推开他,声音陡然拔高:“撞柱殉情?好,
那我问你——表妹撞的是哪根柱子?流了多少血?谁验的伤?谁收的尸?棺材停在哪儿?
灵堂设在哪儿?”一连串的问题,砸得江慎哑口无言。旁边有命妇小声议论:“是啊,
文家姑娘殉情后,灵堂好像确实没设……”“说是文家要接回去厚葬,
可也没见发丧……”“蹊跷,确实蹊跷。”皇后沉声开口:“江氏,你到底想说什么?
”江澜因转身,面向满堂的命妇和朝臣,
一字一句清晰无比:“臣女想说的是——表妹文师师,根本没有死。那天的撞柱,是假的。
那血,是鸡血。那人,是假晕。”满堂哗然。“你、你血口喷人!”江慎气得浑身发抖,
“师师她从小就住在侯府,跟亲妹妹一样!你嫉妒她,也不能这样污蔑她!”“嫉妒?
”江澜因笑了,“我嫉妒她什么?嫉妒她装死骗得满城同情?嫉妒她让我背了十年的黑锅?
还是嫉妒她——”她顿了顿,看向皇后的眼睛:“嫉妒她此刻正跟‘战死’的太子殿下,
在江南双宿双飞?”这一句话,像惊雷炸响在灵堂。“你说什么?!”“太子没死?
”“不可能!战报都传回来了,尸骨都找不到了,怎么会没死?”皇后猛地站起身,
脸色铁青:“江氏,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?污蔑太子,可是死罪!”“臣女知道。
”江澜因不闪不避,“所以臣女敢说这话,自然有证据。”她从袖中取出一封信,高高举起。
“这是太子殿下亲笔写给表妹的信,半个月前送到侯府。臣女的母亲亲手收的,
亲手交给表妹的。信里写什么,诸位一看便知。”江慎脸色刷地白了。
那封信……怎么会在她手里?他想起来了——前天晚上,娘把信看完后随手夹在妆奁里,
而江澜因的房间,就在娘隔壁……皇后盯着那封信,眼神闪烁。半晌,
她缓缓开口:“呈上来。”嬷嬷接过信,呈到皇后面前。皇后展开信,只看了几行,
手就开始发抖。信上确实是太子的笔迹——她认得自己儿子的字。信上写的是江南的风景,
写的是对她的思念,写的是“待风波平息,我便接你过来,我们再也不分开”。
“风波平息”。什么风波?当然是太子“战死”的风波。皇后闭上眼睛,深吸一口气。
她想起这半个月来的种种——儿子“战死”,她悲痛欲绝,几乎哭瞎了眼。
可何家那边却一直劝她节哀,说什么“太子为国捐躯,死得其所”。原来如此。
原来他们都知道。只有她被蒙在鼓里。皇后睁开眼,目光落在江澜因身上。这个女孩,
她以前从没放在眼里。懦弱,胆小,好拿捏——这是她对江澜因的印象。可现在,
这个女孩站在她的灵堂里,当着满朝命妇的面,撕开了她儿子假死的真相。好大的胆子。
“江氏。”皇后沉声道,“这封信,本宫会查。但你——”“皇后娘娘。”江澜因打断她,
“臣女还有一句话要说。”“什么话?”江澜因抬起手,指向自己的胸口。
“臣女被塞进棺材之前,咬破手指,在身上写了血书。”她说,
“血书写的是:若臣女死于非命,必是有人杀人灭口。请皇后娘娘明察。”满堂再次哗然。
血书?在身上写血书?这得是多大的决心,多大的恨意?皇后的脸色彻底沉下来。
她盯着江澜因,目光像刀子一样。这个女孩,比她想象的难缠得多。身上有血书,
就不能让她“死于非命”。当着满朝命妇的面撕开真相,就不能悄无声息地按下去。
她这是把自己的命,赌在了众目睽睽之下。好,很好。“江氏。”皇后缓缓开口,
“你说的事,本宫会彻查。若属实,本宫自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若不属实——”她顿了顿,
语气陡然凌厉:“污蔑太子,诋毁忠烈,诛九族的大罪,你可想清楚了。
”江澜因迎着她的目光,毫不退缩:“臣女想得很清楚。”四目相对,火花四溅。
灵堂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命妇们面面相觑,大气都不敢出。就在这时,
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:“好热闹。”所有人齐齐回头。灵堂门口,逆光站着一个人。
玄色长袍,墨发高束,周身气势冷得像数九寒天。他负手而立,目光越过众人,
落在江澜因身上。摄政王,顾辰枭。太子的亲小叔,当朝皇帝的亲弟弟,
如今手握大权、摄政朝堂的那个人。皇后脸色微变:“王爷怎么来了?
”顾辰枭迈步走进灵堂,靴声橐橐,每一步都像踩在人心尖上。“太子灵堂出了这么大的事,
”他说,声音不疾不徐,“本王来看看,有何不可?”他走到近前,目光从皇后脸上掠过,
最后停在江澜因身上。江澜因抬起头,对上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。上辈子,
她跟这位摄政王没有任何交集。她在甘露寺苦修时,他在朝堂呼风唤雨。她死的时候,
他已经是手握天下的摄政王。可这辈子——她想起大纲里写的情节。她要在灵堂勾引摄政王。
她要从这个棺材里爬出来,一步步走到凤位上。顾辰枭看着她,忽然笑了。笑容很淡,
淡到几乎看不出来,可那眼神,却像能看穿人心。“你就是江澜因?”他问。“是。
”江澜因应道。顾辰枭点点头,没有再多说什么,转身走到一旁坐下,一副看戏的姿态。
皇后深吸一口气,重新看向江澜因:“今日之事,暂且到此。江氏,你先回去,
等本宫查明真相,自会传你。”这是要把她打发走,然后慢慢收拾。江澜因听出来了。
可她不在乎。她要的,只是今天当着满朝命妇的面,
把“太子假死”“表妹假殉情”这两件事撕开一个口子。只要有了这个口子,后面的事,
就好办了。她福了福身:“是,臣女告退。”转身要走。路过顾辰枭身边时,
她脚步微微一顿。眼角余光扫过那张冷峻的脸。摄政王。她未来的路,就从这个人开始。
江澜因没有停留,迈步走出灵堂。身后,江慎追出来,一把拽住她胳膊,
压低声音咬牙切齿:“江澜因,你疯了!你知道你今天做了什么吗?
你这是要把整个侯府都害死!”江澜因低头,看着那只拽着自己胳膊的手。上辈子,
就是这样一只手,把她按在皇后面前,眼睁睁看着刀落下来。她抬起头,看着江慎,
笑了:“大哥,你说什么呢?我做的这一切,不都是为了侯府吗?”“你——”“太子假死,
瞒报军情,这是欺君之罪。我揭穿真相,是救侯府于水火。你不感谢我,怎么还骂我?
”江慎气得浑身发抖:“你、你……”江澜因轻轻抽回胳膊,理了理衣袖。“大哥,
回去告诉爹娘,不用谢我。”她说,“要谢,等表妹回来再谢。”说完,她转身离去。
白色的嫁衣在风中猎猎作响,裙摆拖过汉白玉的地砖,留下一道淡淡的血痕。
那是她指尖滴落的血。江慎站在原地,看着那道越来越远的背影,
心里忽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这个妹妹,从棺材里爬出来之后,
就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任人拿捏的江澜因了。灵堂内。顾辰枭依旧坐在那儿,
目光若有所思地看着门口的方向。刚才江澜因从他身边走过时,他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,
混合着某种若有若无的香气。那种香气,不是脂粉,倒像是——寺庙里的檀香。
一个侯府嫡女,怎么会有檀香的气息?有意思。皇后走过来,压低声音:“王爷,
今日之事……”“皇后不必多言。”顾辰枭站起身,“本王只问一句——太子当真死了吗?
”皇后脸色一僵。顾辰枭看着她的表情,已经知道了答案。他没再说什么,抬步往外走。
走到门口时,他忽然停住,回头看了一眼太子灵前的牌位。“传令下去,”他说,
“派人去江南,查。”“是。”侍卫领命而去。顾辰枭迈步走出灵堂。
外面不知何时飘起了雪,细密的雪花纷纷扬扬,落在他的肩头。他想起刚才那个女孩的眼睛。
那双眼睛里,有恨,有冷,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。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,
才会有的眼神。有点意思。东宫外,江澜因站在雪地里,回头看了一眼巍峨的宫门。
从这里看过去,太子的灵堂隐约可见,白色的孝布在风中飘摇。她静静地看了一会儿,
忽然笑了。“太子殿下,”她轻声说,“好好在江南赏景吧。
等你回来的时候——”她顿了顿,转身离去。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,融化成一滴晶莹的水珠,
顺着脸颊滑落。不知道的,还以为她哭了。可她自己知道,那不是泪。那是重生之后,
第一次感受到的——活着的气息。第二章雪越下越大。江澜因站在东宫外的长廊下,
看着漫天飞雪,一动不动。她身上还穿着那身白色嫁衣,血迹已经凝固成暗红色,
在素白的绸缎上格外刺目。散乱的长发被雪水打湿,贴在脸颊上,冷得彻骨。可她不想动。
她需要想一想,接下来该怎么办。今天在灵堂上,她撕开了太子假死的口子,
也把自己架在了火上烤。皇后不会善罢甘休,侯府那边更不会放过她。等回去之后,
爹娘会怎么对她?上辈子,她没来得及反抗,就被塞进了棺材。这辈子,
她从棺材里爬出来了,可真正的战场,才刚刚开始。“姑娘。”身后传来脚步声,
是她的贴身丫鬟青杏。青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,脸冻得通红,看见江澜因的刹那,
眼泪刷地就下来了:“姑娘!您、您怎么从棺材里出来了?奴婢听说您被塞进去,
差点没吓死……”江澜因转过头,看着这个上辈子唯一对她好过的人。青杏,她的陪嫁丫鬟。
上辈子她被关进甘露寺时,青杏死活要跟着去,伺候了她整整十年,最后死在一场风寒里。
临死前,青杏拉着她的手说:“姑娘,您要好好的,等太子回来,您就熬出头了。
”她哪里知道,太子根本不会来。江澜因抬手,轻轻擦去青杏脸上的泪:“别哭了,我没事。
”青杏一愣。姑娘的声音……怎么不一样了?以前姑娘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,
带着三分怯懦三分讨好,可现在,明明还是那个声音,却让人莫名觉得安稳。“姑娘,
咱们快回去吧。”青杏抹了把眼泪,“侯爷和夫人肯定担心死了。”江澜因笑了。担心?
他们担心的是她,还是担心她这个“棋子”出了岔子,没法向皇后交代?“走吧。”她说。
主仆二人踏着积雪,往侯府的方向走去。雪地里留下一深一浅两行脚印,很快又被新雪覆盖。
镇北侯府,正堂。灯火通明。江澜因的爹——镇北侯江崇山,正背着手在堂中走来走去,
脸色阴沉得像要滴出水来。她的娘张氏坐在一旁,拿着帕子抹眼泪,哭得抽抽噎噎。
大哥江慎站在门口,一脸焦躁地往外张望。“怎么还不回来?”江崇山停下脚步,怒道,
“她一个姑娘家,这么晚不回来,像什么话!”张氏哭着说:“侯爷,您就别骂她了。
她刚从棺材里出来,心里肯定害怕……”“害怕?”江崇山冷笑,“她要是害怕,
就不会在灵堂上说那些疯话!太子假死?表妹没死?她这是要把咱们全家都害死!
”话音刚落,门外传来脚步声。江澜因掀开帘子,走了进来。满身风雪,白衣染血,
散乱的长发披在肩上,整个人看起来狼狈至极。可她的眼睛,却亮得惊人。
江崇山看见她这副模样,先是一愣,随即怒火更盛:“逆女!你还敢回来!”他大步上前,
抬手就是一巴掌。江澜因没有躲。巴掌结结实实地落在脸上,打得她头一偏,嘴角渗出血来。
青杏吓得扑通跪下:“侯爷饶命!姑娘她刚从棺材里出来,身子弱……”“滚出去!
”江崇山一脚踹开她。江澜因慢慢转过头,看向自己的父亲。上辈子,
这个人端着毒药喂到她嘴边,说“因因,你再忍一忍,这辈子就过去了”。她忍了,
然后死了。这辈子,他打她一巴掌,她就得受着吗?不。她不会再受着了。“爹打完了?
”她开口,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,“打完了,女儿有几句话要说。
”江崇山被她的眼神看得心里发毛,下意识退后一步。这个女儿,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?
张氏哭哭啼啼地跑过来,一把抱住江澜因:“因因,我的儿,你怎么这么傻?
你、你怎么能在灵堂上说那些话?你这不是把全家往火坑里推吗?”江澜因低头,
看着这个抱着自己哭的娘。上辈子,她跪在甘露寺里受苦时,娘来看过她一次。
那是她被关进去的第三年,娘站在寺门外,远远地看着她,说:“因因,你别怪娘。
师师她从小没爹没娘,怪可怜的,你就当替她还了这份债。”替她还债。她欠表妹什么?
从小到大,表妹住在侯府,吃穿用度样样跟她一样,她有的,表妹都有。她让着表妹,
哄着表妹,事事以表妹为先。到头来,表妹抢了她的未婚夫,害她丢了性命,她还欠表妹的?
江澜因轻轻推开张氏的手。“娘,”她说,“女儿问你一句话。”张氏一愣:“什么话?
”“那封信,”江澜因看着她,“太子写给表妹的信,是你亲手收的,
也是你亲手交给表妹的。对不对?”张氏脸色刷地白了。江崇山的脸色也变了。
那封信——他们以为处理得干干净净,怎么会落到江澜因手里?“你、你胡说什么?
”张氏结结巴巴,“什么信?我不知道……”“不知道?
”江澜因从袖中取出那封信的副本——原件已经交给了皇后,这是她提前抄录的一份,
“那这封信上的字,娘认不认得?”张氏看着那张纸,嘴唇颤抖,说不出话来。
江澜因看向江崇山:“爹,你知道这封信上写的是什么吗?写的是太子对表妹的思念,
写的是等风波平息就接她过去。太子根本没死,他在江南好好的。表妹也没死,
她陪在太子身边,也好好的。”她顿了顿,声音陡然拔高:“只有我,只有我被塞进棺材里,
给他们当替死鬼!”江崇山的脸色铁青,半晌说不出话。张氏忽然扑通跪下,
抱着江澜因的腿哭起来:“因因,娘求你了,这事你就当不知道行不行?
师师她、她肚子里已经有了太子的骨肉,她要是被揭穿,就是一尸两命啊!
”江澜因低头看着她,眼神复杂。原来如此。原来表妹怀孕了。
难怪太子假死也要带着她私奔,难怪爹娘拼命瞒着这件事,
难怪他们急着把她塞进棺材“配冥婚”——只要她这个正牌未婚妻死了,
表妹就能名正言顺地顶替她的位置。多好的算盘。“所以,”江澜因缓缓开口,
“娘的意思是,让女儿继续当这个替死鬼?”张氏哭得说不出话,只是点头。江澜因笑了。
她蹲下身,与张氏平视。“娘,你知道吗?女儿上辈子——不对,是这辈子被塞进棺材之前,
想过很多事。”她说,“女儿想,从小到大,我哪里对不起表妹?她喜欢我的首饰,我给她。
她想要我的衣裳,我让给她。太子来提亲的时候,她哭着说她喜欢太子,我怎么办?
我能怎么办?”张氏怔怔地看着她。“太子是皇上赐的婚,我能退吗?不能。
”江澜因继续说,“表妹要死要活,我天天哄着她,事事让着她,到头来——”她站起身,
居高临下地看着跪在地上的母亲:“到头来,她还是恨我。恨我挡了她的路,
恨我占了她的位置。所以她跟太子合谋,让他假死,让我配冥婚。
她好清清白白地跟太子在一起,生儿育女,白头偕老。”张氏张了张嘴,说不出话。
江崇山站在一旁,脸色变了又变。江澜因看向他:“爹,你刚才打我,
是因为我在灵堂上说出了真相。可你有没有想过——如果我不说,会是什么下场?
”她一字一顿:“太子假死,瞒报军情,这是欺君之罪。事发之后,侯府满门抄斩,
一个都跑不掉。我揭穿真相,是在救你们。”江崇山浑身一震。这话……有道理。
可他很快反应过来:“你少胡说!太子是何等身份,他怎么会——”“他怎么会这么做?
”江澜因接过话,“因为他要表妹,又不想得罪侯府。让他假死的主意,只怕还是表妹出的。
她一箭双雕,既除了我,又能跟太子双宿双飞。等几年后风声过去,太子‘复活’回来,
她就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。我呢?我就是个死在棺材里的可怜虫,连坟都没有。
”江崇山踉跄后退一步,脸色惨白。他想起师师那丫头临走前看他的眼神,
那种带着三分得意、三分算计的眼神。当时他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,现在看来……“不可能,
不可能……”他喃喃道,“师师她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,她不会……”“她不会?
”江澜因冷笑,“那爹告诉我,她现在在哪儿?”江崇山哑口无言。是啊,师师在哪儿?
“殉情”之后,她的尸体被文家接走了,说是要厚葬。可文家根本没发丧,灵堂都没设。
这半个月来,他们忙着操办冥婚的事,谁也没顾上去想——师师的“尸体”,到底埋在哪儿?
现在想来,那根本就是个空棺材!江澜因看着他的表情,知道他想明白了。她转身,往外走。
“站住!”江崇山喊住她,“你要去哪儿?”“回房。”江澜因头也不回,“明天一早,
皇后应该会传我进宫对质。我总得睡个好觉,才有精神应对。”江崇山愣住了。
皇后传她对质?她怎么知道的?江澜因没有解释,掀开帘子走了出去。青杏连忙爬起来,
追了上去。正堂里,只剩下江崇山夫妻俩,一个站着,一个跪着,相顾无言。过了很久,
张氏才颤声道:“侯爷,咱们……咱们是不是做错了?”江崇山没有回答。窗外,雪还在下。
第二天一早,皇后果然传旨,召江澜因进宫对质。来接她的太监态度出奇地好,
一路上点头哈腰,满脸堆笑:“江姑娘,您慢着点儿,地上滑,小心摔着。
”江澜因看他一眼。这个太监她认识,是皇后身边最得力的内侍,姓孙,
上辈子就是他去甘露寺传的旨——砍她一只手的旨意。那时候,他可不是这副嘴脸。
“孙公公。”江澜因开口。孙太监一愣:“江姑娘认得奴才?”“不认得。”江澜因笑了笑,
“只是觉得公公面善。”孙太监讪讪地笑,不敢接话。一行人进了宫,穿过重重宫门,
最后停在坤宁宫门口。江澜因抬头看着那三个字,深吸一口气。上辈子,
她就是在这座宫殿里,被砍了一只手。这辈子,她不会再跪着进去了。“江姑娘,请。
”孙太监推开门。江澜因迈步走了进去。坤宁宫内,暖意融融。皇后高坐在凤座上,
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,好像昨天灵堂上的对峙从没发生过。旁边坐着几位命妇,
都是皇后的心腹。可江澜因的目光,却被另一个人吸引。顾辰枭。摄政王坐在一旁,
手里端着茶盏,正慢条斯理地喝茶。看见她进来,他抬眼一扫,嘴角微微勾起。那眼神,
像是在看一场好戏。江澜因收回视线,走到殿中央,福身行礼:“臣女参见皇后娘娘,
参见摄政王。”“起来吧。”皇后笑容满面,“赐座。”宫女搬来绣墩,放在一旁。
江澜因却没有坐。她抬起头,看向皇后:“皇后娘娘召臣女来,想必是查清了太子殿下的事?
”皇后的笑容僵了一瞬。这个丫头,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。“本宫昨日派人去江南查访,
”皇后缓缓开口,“确实查到了一些线索。”她顿了顿,看向江澜因。按规矩,
这时候江澜因应该诚惶诚恐地问“什么线索”,然后她就可以掌握主动权。
可江澜因只是静静地站着,一言不发,等着她往下说。皇后脸色微沉。这个江澜因,
怎么不按常理出牌?坐在一旁的顾辰枭轻笑一声,放下茶盏:“皇后有话直说就是。
江姑娘从棺材里爬出来,胆子大得很,吓不着的。”这话听起来像是替江澜因说话,
可江澜因却听出了几分调侃的意味。她看向顾辰枭,正对上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。四目相对,
电光火石。江澜因率先移开视线。皇后深吸一口气,沉声道:“江氏,
你昨日在太子灵前说的话,本宫已经查实了。”满殿寂静。江澜因的心猛地一跳。查实了?
这么快?“太子……确实没死。”皇后说出这句话时,脸上闪过一丝痛苦,
“他、他瞒着本宫,假死私奔,与文氏藏匿江南。本宫也是昨日才知道。”说着,
她眼眶泛红,拿起帕子拭泪:“本宫十月怀胎生下的儿子,竟然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,
本宫……本宫愧对列祖列宗,愧对满朝文武!”几位命妇连忙上前劝慰:“娘娘节哀,
太子殿下年轻,一时糊涂……”“糊涂?”皇后哭道,“这是糊涂的事吗?假死瞒报,
欺君罔上,这是要杀头的大罪!”江澜因静静地看着这一幕。哭得真好。
如果不是上辈子亲眼见过这个人砍她手时的冷酷无情,她都要被感动了。可她知道,
皇后这眼泪,三分真,七分假。太子假死,皇后未必不知情。就算一开始不知道,
这半个月来,何家的人轮番进宫劝她“节哀”,她难道就没起疑心?现在事情败露,
她先把自己摘干净,把儿子推出去顶罪——反正太子是她亲生的,就算回来受罚,
也罪不至死。而江澜因这个揭穿真相的人,反倒成了“害太子落罪”的罪人。好算计。果然,
皇后哭了一阵,抬眼看江澜因:“江氏,本宫知道你受了委屈。你放心,等太子回来,
本宫一定严惩不贷,给你一个交代。”江澜因福身:“多谢娘娘。
”皇后又道:“至于文氏——那个贱人,勾引太子,蛊惑他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,
本宫绝不会轻饶。等他们回来,本宫定要……”“皇后娘娘。”江澜因忽然开口打断她。
皇后一愣:“怎么?”“臣女斗胆,想问娘娘一件事。”皇后皱眉:“何事?
”“文师师‘殉情’那日,娘娘可在场?”皇后脸色微变:“本宫不在。
”“那娘娘可曾亲眼见过文师师的‘尸体’?”“……不曾。
”“那娘娘可曾派人验过那血是真是假?可曾确认过她是不是真的死了?”皇后说不出话来。
江澜因转向那几位命妇:“诸位夫人,那日在场的人不少。
臣女想请教几位——那日文师师撞柱,你们可看清了?”命妇们面面相觑,不敢接话。
江澜因笑了笑:“既然都不说话,那就让臣女来说。”她从袖中取出一张纸,展开。
“这是文师师身边丫鬟的供词。”她说,“丫鬟叫春杏,今年十五岁,
是文师师从文家带过来的。她亲眼看见,那日文师师撞柱之前,
往袖子里藏了一个血囊——里面装的是鸡血。”满殿哗然。“鸡血?!”“怎么可能?
”“那血明明流了一地……”江澜因继续说:“撞柱的时候,她只是轻轻碰了一下柱子,
然后捏碎血囊,自己咬破舌尖,假装昏死过去。从头到尾,她根本没受一点伤。
”皇后的脸色铁青。命妇们目瞪口呆。江澜因收起供词,看向皇后:“皇后娘娘若是不信,
可以传春杏来对质。她是文师师的贴身丫鬟,文师师去哪儿,她最清楚。
文师师是假死还是真死,她也最清楚。”皇后张了张嘴,说不出话。
她知道春杏这个人——确实是文师师的丫鬟,从小就跟着文师师,形影不离。
如果春杏都招了……“这个贱人!”皇后咬牙切齿,“她竟敢、她竟敢……”“娘娘息怒。
”江澜因不疾不徐地说,“文师师假殉情是真,太子假死也是真。
臣女斗胆猜测——这两人恐怕早就私定终身,只等着臣女这个‘碍事’的死了,好双宿双飞。
”她顿了顿,语气陡然转冷:“只可惜,臣女命硬,从棺材里爬出来了。
”殿内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命妇们大气都不敢出,悄悄交换着眼神。这个江澜因,
胆子也太大了。当着皇后的面,把太子的丑事一件件抖落出来,这不是打皇后的脸吗?
皇后果然怒了。她猛地站起身,脸色铁青:“江氏,你——”“娘娘息怒。
”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。顾辰枭站起身,走到江澜因身边,看向皇后。
“江姑娘说的句句属实,证据确凿。”他说,“本王已经派人查过,那春杏确实招了,
文师师也确实没死。至于太子——”他顿了顿,语气淡然:“本王的人昨日在苏州找到他,
正押送回京。”皇后踉跄后退一步,跌坐回凤座上。押送回京。这就是说,太子假死的事,
已经板上钉钉,无可辩驳了。她看向顾辰枭,目光复杂。这个小叔子,
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太子。现在太子出了这种事,他只怕正等着看笑话呢。
顾辰枭仿佛没看见皇后的目光,转头看向江澜因。“江姑娘,”他说,
“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,想要什么补偿?”江澜因抬头看他。补偿?上辈子,她什么都没要,
什么都没争,最后落得个惨死的下场。这辈子,她要的,不是什么补偿。“王爷说笑了。
”她微微一笑,“臣女揭穿真相,不是为了要补偿。”“哦?”顾辰枭挑眉,
“那为的是什么?”江澜因迎着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,一字一顿:“为的是让该死的人,
死得明明白白。”顾辰枭眼底闪过一丝兴味。这个姑娘,果然有意思。他低低笑了一声,
收回目光,对皇后道:“娘娘,既然事情已经查清,本王就先告退了。等太子回京,
再行处置。”说完,他大步往外走。路过江澜因身边时,他脚步微微一顿,
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:“想要补偿,随时来找本王。”江澜因心头一跳。
等她抬头时,顾辰枭已经走出殿外,消失在茫茫雪色中。皇后坐在凤座上,脸色阴晴不定。
过了很久,她才缓缓开口:“江氏,你先回去吧。等太子回京,本宫自会给你一个交代。
”江澜因福身告退。走出坤宁宫时,雪还在下。青杏撑着伞迎上来,满脸担忧:“姑娘,
怎么样?皇后没为难您吧?”“没有。”江澜因接过伞,“走吧。”主仆二人踏雪而行。
走到半路,江澜因忽然停下脚步,回头看向坤宁宫的方向。高高的宫墙,层层叠叠的殿宇,
在漫天飞雪中显得格外巍峨。上辈子,她跪在这座宫里,被砍了一只手。这辈子,
她站着走出去。这才刚刚开始。“姑娘?”青杏疑惑地看着她。江澜因收回视线,
笑了笑:“没什么,走吧。”雪越下越大。她撑着伞,一步一步,走得很稳。身后,
那行脚印很快被新雪覆盖,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她知道,从今天起,一切都不同了。
太子假死的事已经揭开,表妹假殉情的事也已经败露。等他们回京,就是一场好戏。而她,
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江澜因。她是——从棺材里爬出来的人。第三章雪下了三天三夜,
到第四日才停。这三天里,京城发生了许多事。太子假死的消息不胫而走,满城风雨。
有人骂太子荒唐,有人叹皇后可怜,更多的人,
把目光投向江澜因——那个从棺材里爬出来、亲手撕开真相的侯府嫡女。茶楼酒肆里,
说书先生把她的事编成段子,绘声绘色地讲:“话说那江家姑娘,被亲哥塞进棺材,
要给‘战死’的太子配冥婚。棺材盖一合,她咬破手指,在身下写下血书——诸位猜猜,
写的什么?”“写的什么?”台下听众齐声问。“写的是——江澜因在此,拜谢诸位!
”满堂喝彩。“这姑娘硬气!从棺材里爬出来,当着皇后和满朝命妇的面,
把那假殉情的表妹撕了个底朝天!鸡血!假的!太子根本没死!在江南跟那表妹双宿双飞呢!
”“好!”“就该这样!”“那表妹人呢?抓回来没有?”“抓了抓了,
摄政王的人亲自去江南拿的,这会儿正押解回京呢!”类似的对话,在京城各个角落上演。
而侯府这边,却是另一番光景。江澜因被禁足了。从宫里回来的当天晚上,江崇山就下令,
把她关进后院的小佛堂,不许任何人探视。“在太子回京之前,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!
”江崇山站在佛堂门口,脸色铁青,“再敢出去惹事,我打断你的腿!”江澜因跪在蒲团上,
背对着他,一言不发。江崇山等了片刻,没等到任何回应,气哼哼地摔门走了。
青杏被关在门外,急得直哭:“姑娘!姑娘您别怕,奴婢想办法救您出去……”“不必。
”江澜因的声音从门缝里传出来,平静得很,“你回去好好待着,别惹他们。
”“可是姑娘……”“听话。”青杏咬着唇,含泪点头。脚步声远去。佛堂里恢复了寂静。
江澜因跪在蒲团上,抬头看着面前的佛像。这是一尊观音像,慈眉善目,手持净瓶。
佛前供着长明灯,灯芯噼啪作响,映得她的脸忽明忽暗。上辈子,她在甘露寺跪了十年,
跪的就是这样的佛像。她一遍遍磕头,一遍遍诵经,一遍遍求菩萨保佑太子在天之灵安息,
保佑表妹早登极乐。现在想来,真是可笑。菩萨要是真有灵,怎么会看着她受苦十年,
最后被毒死?江澜因慢慢站起身,走到佛像前,伸手拿起那盏长明灯。灯油温热,火焰跳跃。
她盯着那簇火苗看了很久,忽然松开手。“啪——”长明灯摔在地上,灯油泼洒,
火焰瞬间蔓延开来。江澜因静静地看着火舌舔上佛龛,舔上经幡,舔上那扇紧闭的木门。
然后,她放声大喊:“走水了!快来人!走水了!”侯府顿时乱成一团。
下人们提着水桶冲进来时,小佛堂已经烧了大半。火光照亮了半边天,浓烟滚滚,
呛得人睁不开眼。“姑娘呢?!姑娘在哪儿?!”“还在里面!快救人!”江崇山闻讯赶来,
脸色煞白。他虽然恼这个女儿,可她要是烧死在佛堂里,他怎么向皇后交代?“愣着干什么?
!快进去救人!”几个家丁硬着头皮冲进火海,不多时,架着一个浑身湿透的人冲了出来。
江澜因裹着被水浸透的棉被,脸色苍白,咳嗽不止。可她的眼睛,却亮得惊人。
“咳咳……多谢爹救命之恩。”她虚弱地说。江崇山看着她,忽然明白了什么。
这小佛堂的火,只怕是她自己放的。“你——!”“爹,”江澜因打断他,声音压得很低,
“您要是再关着我,我就一把火把侯府全烧了。说到做到。”江崇山瞪着她,气得浑身发抖。
这个女儿,真的疯了。不,不是疯了。是换了个人。从棺材里爬出来之后,
她就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江澜因了。“……滚!”江崇山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,
“滚回你自己院子去!”江澜因笑了。她裹紧棉被,在青杏的搀扶下,一瘸一拐地走了。
身后,小佛堂还在燃烧,火光映在她的背影上,拖出一道长长的影子。三日后,太子回京。
没有锣鼓喧天,没有百官迎接。摄政王的人押着他,从侧门悄悄进城,直接送进了宫里。
同行的,还有文师师。江澜因是在佛堂纵火的第二天收到这个消息的。
送消息的人是顾辰枭的侍卫,一个面无表情的年轻人。“王爷让属下转告江姑娘,
”那侍卫说,“太子和文氏明日到京。姑娘若想去看热闹,明日午时,东宫门口。
”江澜因看着那侍卫,忽然笑了。“王爷这是请我去看戏?”侍卫没接话,拱了拱手,
转身离去。青杏在一旁紧张地问:“姑娘,您去吗?”江澜因站起身,走到窗前。窗外,
雪后初晴,阳光照在积雪上,刺得人眼睛疼。“去。”她说,“当然去。”她等这一天,
等了三天。不,等了十年。第二天午时,江澜因准时出现在东宫门口。
她换了一身打扮——素白的袄裙,外罩银鼠皮斗篷,头上只簪一支白玉兰花簪。
整个人清素雅致,却又透着几分说不出的矜贵。这是她特意选的。上辈子,
她在甘露寺穿惯了粗布衣裳,这辈子,她要让某些人看看,谁才是该穿绫罗绸缎的人。
东宫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。有看热闹的百姓,有探头探脑的官员家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