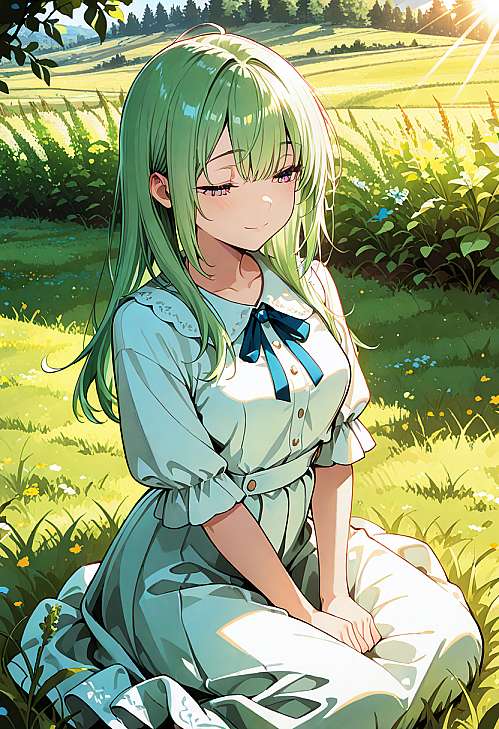林晚,曾是太医院院使之女,一夕家道中落,被一顶小轿抬入镇北将军府,
成了给重伤昏迷的少将军冲喜的“工具”。
面对的是满府异样的目光、病榻上无声的夫君、神色愁苦的公婆,
以及那位迫不及待想将将军府中馈攥在手中的偏心老夫人。合卺酒凉,
我望着红纱帐内那张英挺却苍白的脸,低语如誓:“夫君,既拜了天地,此后你的府邸,
你的家人,便由我来守护。”01子时三更,梆子声渗过镇北将军府的高墙,
落在西厢新房外便碎了。两根儿臂粗的喜烛烧得正旺,烛泪堆成猩红的小山,
将满屋“囍”字映得晃眼,也映亮榻上那张过分苍白的脸——她的夫君,镇北少将军贺兰渊。
三日前的喜轿从侧门进,没有拜堂,没有合卺。她,柳衔枝,前太医院院使之女,
如今只是贺家从破落户里挑来“冲喜”的工具。烛火“噼啪”爆开一星。
榻上人指尖几不可察地一颤。柳衔枝搁下手中银针,帕子还未擦净指腹,
门外骤起刺耳的拍门声——“少夫人!老夫人传您即刻去松寿堂问话!”声音尖利,
裹着毫不掩饰的怠慢。陪嫁丫鬟芸香吓得一抖。柳衔枝缓缓抬眼,望向铜镜。
镜中人凤冠未卸,喜服未褪,一张脸在跳跃的烛光里静得瘆人。她将银针收入袖中,
指尖触到冰冷针囊时,轻轻合拢。“更衣。”声音落进死寂的夜,像颗投入寒潭的石子。
02松寿堂的檀香浓得呛人。柳衔枝踏入堂内时,满屋视线如针般扎来。上首坐着贺太夫人,
一身赭色福寿纹袄,手里捻着佛珠,眼皮未抬。下首是公公贺镇山与婆婆周氏,
二人面色复杂。另一侧,二婶赵氏嘴角噙着笑,毫不掩饰打量货物般的目光。
“新妇来得迟了。”太夫人声音不高,却让堂中空气一凝。柳衔枝依礼下拜,奉茶。
太夫人不接,只垂眼瞧她:“既进了贺家的门,便要守贺家的规矩。你既是为冲喜而来,
首要便是心诚。你的嫁妆单子,稍后交给赵氏,一并收入公中库房,也算为你夫君积福。
”堂内鸦雀无声。将新娘私产充公,这是明晃晃的掠夺。周氏攥紧了帕子,贺镇山眉头紧锁,
却未出声。赵氏笑道:“母亲说得是,侄媳妇放心,婶娘定替你管得妥妥帖帖。
”柳衔枝举着茶盏的手臂稳如磐石。她抬眼,目光清凌凌地望向太夫人:“祖母慈训,
孙媳谨记。只是孙媳昨夜观夫君气色,郁结深重,恐冲喜之事,首重府内‘和气生旺’。
孙媳不才,略通医理,见祖母眼下青黑,脉象或有些许浮滑,可是近日多梦惊悸?
”太夫人捻佛珠的手一顿。柳衔枝缓缓将茶盏置于她手边小几,
声音温顺却清晰:“孙媳愿为祖母拟一安神方,佐以饮食调摄。祖母安泰,
才是阖府最大的福气。”太夫人盯着她,浑浊的眼底第一次闪过一丝审视的冷光。半晌,
她接过那杯已然半凉的茶,抿了一口。“倒是个有心的。”茶盏落案的轻响,
像一声暂歇的锣。03从松寿堂出来,日头已高。周氏悄然落后两步,与柳衔枝并肩。
“好孩子,”她声音很低,带着未散的颤,“方才……委屈你了。”柳衔枝侧首,
见这位将军夫人眼眶微红,并非作伪。“母亲言重,是儿媳本分。”周氏摇头,欲言又止,
最终只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:“渊哥儿的院子……你多费心。缺什么,只管遣人来跟我说。
”这话里,有歉意,也有无力,更有一丝托付的意味。柳衔枝颔首:“儿媳明白。
”回到“澄渊院”,她并未歇息。先是为贺兰渊例行施针,
指腹感受着他腕间微弱却逐渐规律的脉搏,心中稍定。随后,她唤来院中所有仆役,共八人。
“我初来乍到,不识诸位,”她坐于廊下,声音不高,却让交头接耳声息了下去,
“只问三件事:谁原在少爷身边伺候?谁管院内洒扫膳食?谁领月钱,从何处领?
”一阵沉默后,一个瘦削的婆子颤巍巍上前:“老奴陈婆,
原在少爷书房奉茶……少爷出事後,便被调去浆洗房了。
”另一个中年仆妇也站出来:“奴婢王婶,管院内小厨房。
月钱……月钱一直是二夫人那边的李妈妈分发,常迟个三五日,还要扣些名目。
”柳衔枝静静听着,目光掠过众人神色。有惶惑,有观望,亦有如陈婆般隐带不平的。
“从今日起,”她开口,字字清晰,“陈婆调回近前伺候。王婶仍管小厨房,
每日用度直接报与我。月钱,每月初五,由芸香在此院发放,足额,不扣。”众人皆是一怔,
随即,几人眼中明显亮起光来。“但,”柳衔枝话音一转,“我院中之人,须谨守本分,
眼明心亮。若吃里扒外,或怠慢少爷——”她没说完,只将手中一枚未用的银针,
轻轻扎进身旁盆栽的叶片中。针尖透叶而过,在日光下闪着一点寒芒。
仆役们齐齐低下头:“谨遵少夫人吩咐。”04安稳不过三日。第四日清早,
柳衔枝正为贺兰渊行针,院门便被不轻不重地叩响,带着一股子刻意拿捏的腔调。
芸香去应门,片刻后回来,脸色不大好看:“少夫人,是二夫人身边的李妈妈,
带了两筐‘时新瓜果’,说是二夫人惦念少爷,特地送来。
”柳衔枝指下银针稳准地落下最后一穴,这才缓缓收手。“请进来。”李妈妈进门时,
腰板挺得笔直,一双三角眼先往榻上扫了扫,才落到柳衔枝身上,
敷衍地福了福:“给少夫人请安。我们夫人说了,少爷病着,少夫人年轻不知事,
怕底下人伺候不用心,特让老奴带些新鲜物儿来,也给少夫人院里添点人气。”话里话外,
直指她“年轻不知事”,连自家院子都管不好。柳衔枝净了手,
目光掠过那两筐确实水灵的瓜果,最后落在李妈妈腕间——那里露出一截明晃晃的赤金镯子,
成色极新,绝非一个管事妈妈该有的份例。“二婶有心了。”她语气平淡,“李妈妈辛苦,
芸香,看茶。”李妈妈却不坐,反而在屋里踱了两步,目光挑剔地扫过屏风、案几,
最终停在柳衔枝还未收起的针囊上。“少夫人这是……亲自为少爷诊治?”她拖长了调子,
“不是老奴多嘴,这金针渡穴的功夫可深得很,若是稍有差池……”“李妈妈。
”柳衔枝打断她,声音不高,却让李妈妈后面的话卡在了喉咙里。她抬起眼,目光清凌凌的,
像能照透人心:“妈妈在二婶身边伺候多年,想必最懂规矩。主子的事,
何时轮到奴才来‘担心差池’了?”李妈妈脸皮一僵。“还是说,”柳衔枝站起身,
缓步走到她面前,声音压得更低,只两人能听清,“妈妈是奉了谁的命,特地来提醒我,
要‘谨守本分’,莫要‘多事’?”李妈妈被她目光慑住,下意识后退半步,
腕上金镯磕在筐沿,“当”一声脆响。柳衔枝却已移开视线,仿佛方才的压迫感从未存在。
“瓜果我收下了,替我谢过二婶。芸香,送李妈妈出去。”李妈妈张了张嘴,
终究没敢再说什么,悻悻退了出去。人一走,柳衔枝看向那两筐瓜果,
对芸香道:“仔细检查,分与院中人食用。若有异样,立刻来报。”这哪里是送瓜果。
这是投石问路,更是警告。05李妈妈走后,澄渊院表面恢复了平静,暗流却开始涌动。
先是小厨房的王婶来报,说去大厨房领每日的米粮肉蔬,被各种推诿,
要么说“今日份例已领完”,要么给些陈米蔫菜。月钱发放日将近,芸香去二房那边询问,
也被李妈妈以“账目未核清”为由挡了回来。经济上的钳制,悄然收紧。柳衔枝不动声色。
她让王婶暂且用私房钱在外采买,不动声色地记下每一笔开销。同时,
她开始更频繁地“路过”府中几处关键地方。这日晌后,她借口为贺兰渊寻一味安神香料,
去了趟库房附近。管事的是个姓钱的老账房,见是她,态度恭敬却疏离:“少夫人,
香料皆在二夫人处登记造册,老奴无权擅动。”柳衔枝不以为意,
目光却扫过他桌上摊开的一本旧账册——那是去岁庄子上缴粮租的明细。她记忆力极佳,
只一眼,便记下几行关键数字:某处田庄亩产数目,与父亲昔日闲聊时提过的上等田标准,
相差近三成。“是我唐突了。”她温声道,转身欲走,又似随口问,
“听闻府中在南街有两间绸缎铺,生意颇佳?不知如今是哪位掌柜打理?
”钱账房眼神闪烁了一下:“是…是二夫人娘家的一位表亲在照看。”柳衔枝颔首,
不再多言。回到澄渊院,她闭目静坐,
日所见缓缓勾连:赵氏腕上新添的翡翠镯子;李妈妈不合身份的金镯;二房那位嫡子贺文柏,
前几日似乎新得了匹价值不菲的西域骏马……而公婆所居的正院,夏日里却连冰例都减了半。
她铺开纸笔,虽无完整账册,却凭着零星信息与心算,勾勒出一张粗糙的脉络图。
箭头从各处产业指向二房,中间损耗的数字,触目惊心。芸香悄声进来,低语:“小姐,
陈婆悄悄递了话,说她有次撞见李妈妈酒后失言,抱怨‘那老东西贪得无厌,
好处都让她娘家捞了去’,说的像是……太夫人。”柳衔枝笔尖一顿。若太夫人也参与其中,
甚至默许二房侵吞,那这便不是简单的妯娌倾轧。而是长房这一脉,正在被慢性抽血,
直至枯竭。窗外暮色渐沉,她看向榻上依旧沉睡的贺兰渊。“看来,有人不想让你醒来。
”她轻声说,眼中最后一丝温存褪去,只剩下冰冷的清明。06线索如碎珠,需一根线串联。
柳衔枝的线,是贺兰渊每日的药渣。自察觉药方可能有问题后,她并未声张,
只将每日煎煮后的药渣悄悄收起一部分,晾干收好。同时,她以“斟酌药性”为由,
向婆婆周氏求来了府中公中药库的出入记录副本——周氏掌管中馈名存实亡,这点权力尚有。
这夜,她将连日积攒的药渣铺在素白棉布上,就着灯烛细细分辨。
父亲留下的那本医案就摊在膝头,徐老赠与的那本则搁在手边。药渣中,
除了太医开具的安神续骨之品,几味不起眼的辅料引起了她的注意:当归须、炒蒲黄。
单看无奇,甚至有益血行。但若与方中另一味主药 “血竭” 长期同用,
据徐老医案中一则偏僻记载,会悄然延缓生机恢复,令人长期昏沉,脉象却显“平稳”,
极难察觉。而公中药库的记录显示,这两味辅料的采购量,近半年来远超常例。谁加的?
为何加?柳衔枝指尖冰凉。这不是庸医误用,而是精巧的毒计。窗外传来细微响动。
她迅速收起药渣与账册,吹熄近处烛火。片刻后,芸香引着陈婆,
从后角门悄无声息地闪了进来。
陈婆老脸在昏暗光线下显得苍白:“少夫人……老奴、老奴今日去浆洗房取少爷旧衣,
撞见李妈妈鬼鬼祟祟跟药房的小学徒嘀咕,塞了包东西过去。老奴留了心,等他们走远,
在草丛里找到了这个……”她颤抖着手,递过来一个小纸包,
里面是几粒尚未煎煮的、品相极佳的炒蒲黄。“李妈妈还说了句,‘老规矩,月底结’。
那小学徒吓得直哆嗦。”柳衔枝接过纸包,药香钻入鼻尖,却带着股寒意。
李妈妈是赵氏心腹,赵氏管家,药房采购……一条线,清晰了。“陈婆婆,
”她声音稳得听不出一丝波澜,“今日之事,烂在肚里。日后,
你只管留意府中与二房、太夫人母家有往来的生面孔,或不同寻常的银钱货物走动。
”陈婆重重点头,佝偻着身子退下了。芸香忧心忡忡:“小姐,他们这是要一直害少爷吗?
我们是不是该告诉将军和夫人?”柳衔枝望着跳跃的烛火,摇了摇头:“无凭无据,
单靠药渣和下人一面之词,动不了盘根错节的二房,更动不了祖母。反而会打草惊蛇。
”07机会比预想中来得快。三日后是贺太夫人的六十寿辰。虽非整寿,
但二房为表孝心亦是彰显管家之权,力主操办一场家宴,遍请族中亲眷。
请柬送至澄渊院时,柳衔枝正将一枚新制的安神香囊系在贺兰渊枕边。她拈着那洒金笺子,
看了片刻,对芸香道:“去回话,说我定当备礼赴宴。”芸香不解:“小姐,
那宴上定是……”“正因如此,才非去不可。”柳衔枝目光落在贺兰渊沉静的睡颜上,
“有些戏,人少唱不起来。”她开始“精心”准备。先是亲自去库房,
在钱账房略显惊愕的目光中,“查阅”了几样寿礼的规格旧例,
又“无意”间问起往年寿宴采买的账目如何走,二夫人如何审核。钱账房答得谨慎,
但她已听出关键:大宗采买,皆由赵氏娘家兄弟经手。紧接着,
她以“为祖母抄经祈福需静心”为由,向周氏讨了府中佛堂隔壁一间小书房几日使用权。
那佛堂,正是太夫人每日清晨必去之处。寿宴前夜,柳衔枝在书房“抄经”至深夜。离去时,
“不慎”将一本簿册遗落案上。簿册封面无字,
内里却夹杂着几页她精心“整理”过的摘要——并非真账,
而是依据她心算推演出的、几处田庄铺面“应有”收益与“账载”收益的惊人对比数字,
旁边以极小字备注了疑似经手人皆指向赵氏亲信。最后,
用她模仿贺兰渊病前笔迹的字体,写了一句模糊的疑问:“二房账目不清,恐伤家族根本,
待吾愈后查之。”这簿册,
她确保会被每日清晨最早去佛堂打扫的、太夫人信任的哑婆子捡到。哑婆子不识字,
但必会交给太夫人。宴无好宴。她便先送上一道“开胃小菜”。寿宴当日,
澄渊院众人领到的月钱果然又被拖延。王婶咬牙用柳衔枝的私己钱垫上,气得眼睛发红。
柳衔枝对镜理妆,镜中人眉眼沉静,唇上点了淡淡胭脂。“走吧。”她起身,
素白衣裙外罩了件水青色褙子,清爽得不沾一丝戾气。踏出院子时,她回头望了一眼。
08寿宴设在府中最大的花厅“锦华堂”。贺家族亲来了不少,衣香鬓影,笑语喧阗,
仿佛一派和睦。柳衔枝到得不早不晚,奉上一尊亲手绣制的《松鹤延年》炕屏作寿礼,
针脚细密,寓意吉祥,无可挑剔。太夫人端坐主位,受了礼,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一瞬,
平淡道:“有心了。”那一眼,比往日多了几分难以捉摸的审视。
柳衔枝垂首退至周氏下首坐下,安然若素。宴过三巡,气氛正酣。赵氏满脸堆笑,
正亲自为太夫人布一道珍稀的鲥鱼,嘴上说着吉祥话。几位族老也在夸二房孝顺,办事周到。
就在这时,厅外忽然传来一阵压抑的骚动和哭嚷声。一个管事模样的人急匆匆进来,
到贺镇山身边低声急语。贺镇山脸色骤然一沉。“何事喧哗?”太夫人不悦地搁下筷子。
贺镇山起身,拱手道:“母亲,是……府里几户家生子的老仆,跪在外头,
说、说他们家中有人急病,月钱迟迟不发,无钱请医抓药……”他声音艰涩,
目光不由自主扫向赵氏。满堂笑语戛然而止。赵氏笑容僵在脸上,
忙道:“定是下面人办事不力!母亲息怒,我这就去……”“二婶且慢。
”柳衔枝的声音清清泠泠地响起。众人目光齐刷刷聚来。只见她缓缓起身,行至厅中,
对着太夫人与贺镇山深深一福:“祖母,父亲,此事恐非下人办事不力这般简单。
孙媳近日整理夫君旧物,偶然见得夫君病前随笔,其中提及府中数处产业账目似有不清,
忧心忡忡。孙媳本不敢妄言,但见今日老仆哭诉,想起夫君忧思,心中实在难安。
”她语速平缓,字字清晰,却像冷水滴入沸油。“你胡说什么!”赵氏尖声打断,
脸涨得通红,“渊哥儿昏迷已久,何来随笔?你休要在此搬弄是非!”柳衔枝抬眼,
目光平静无波:“二婶勿急。孙媳只是转述夫君疑虑。况且,”她话锋微转,
“孙媳略通医理,近日为夫君调理,发现药渣中有些不该出现的辅料,与药性相冲,
恐于康复不利。此事,或许也该查查。”“药渣”二字一出,赵氏脸色唰地白了。
坐在她身旁的李妈妈,更是控制不住地抖了一下。太夫人捻着佛珠的手停了。
她看看面色惨白的赵氏,又看看镇定自若的柳衔枝,最后,
目光落在自己儿子贺镇山铁青的脸上。厅内死寂,只闻呼吸声。族亲们面面相觑,
交换着惊疑不定的眼神。这寿宴,味道彻底变了。柳衔枝依旧站着,
水青色的衣衫在满堂华彩中显得格外素净,也格外扎眼。09满堂寂静,落针可闻。
太夫人手中的佛珠,终于又缓缓捻动起来,一颗,一颗,摩擦出细微的沙沙声,
压在每个人心头。“账目不清……”她缓缓开口,声音听不出喜怒,
“药性有疑……今日是我寿辰,倒是听了不少新鲜事。”赵氏噗通一声跪下,
眼泪说来就来:“母亲明鉴!儿媳管家兢兢业业,从无半点私心!
定是、定是有人见儿媳辛苦,心生妒忌,故意陷害!”她猛地指向柳衔枝,“是她!
自她进门,府里便无一日安宁!”柳衔枝并未辩驳,只是静静站着,目光坦然迎向太夫人。
贺镇山胸膛剧烈起伏,猛地一拍桌案:“够了!”他虎目圆睁,看向赵氏,“账目之事,
今日起,由你大嫂会同账房重新核对!至于药渣……”他声音发颤,转向柳衔枝,“衔枝,
你所言当真?”“儿媳不敢妄言。”柳衔枝从袖中取出早已备好的小纸包,
正是陈婆捡到的那包炒蒲黄,以及她誊抄的药性相冲记录,“此物出现在夫君药渣中,
与方中血竭同用,久服恐滞碍生机。药渣样本与药库出入记录,儿媳已另行封存,
父亲随时可查。”证据确凿,并非空口白话。周氏早已泪流满面,紧紧攥住贺镇山的衣袖,
无声哀求。太夫人闭上了眼。半晌,才道:“渊哥儿的事,是头等大事。赵氏,你管家不利,
生出这许多风波,即日起,中馈之事,暂由你大嫂协同衔枝料理。至于药房一干人等,
全部拘起,由老大亲自审问。”“母亲!”赵氏失声。这已不是敲打,
是实实在在的分权与问责。“至于你,”太夫人睁开眼,看向柳衔枝,目光复杂,
“关心则乱,其情可悯。但家宅安宁,重于一切。今日之事,到此为止,不可再外传,
亦不可再擅自查探,明白吗?”这是警告,也是盖棺定论。她保下了二房的体面,
也暂时压下了风波。柳衔枝垂下眼帘:“孙媳谨遵祖母教诲。”她知道,今日只能到此。
彻底扳倒盘根错节的二房,仅靠一次突击远远不够。但目的已达到:公婆态度彻底转向,
她获得了部分管家权,药房线索握在手中,而太夫人心中那根刺,已深深埋下。
宴席不欢而散。回到澄渊院,芸香才敢大喘气:“小姐,太夫人还是偏着他们!
”柳衔枝卸下外衫,语气平静:“意料之中。但风向,已经变了。”她走到贺兰渊榻边,
轻声道,“你瞧,我们进了一步。”窗外,浓云遮月,夜色如墨。10风波并未平息,
反而转入地下,更为凶险。赵氏虽暂失管家之权,但多年经营,爪牙遍布。
账目核对进展缓慢,关键账册“意外”受潮霉烂;药房被拘之人个个咬紧牙关,
只推说抓错药,无人指认李妈妈。与此同时,新的流言在府内外滋生:少夫人柳氏,
为掌权不惜构陷婶母,甚至质疑太夫人治家不公,实乃“搅家精”。压力再次回到澄渊院。
这日午后,柳衔枝正在查看贺镇山移交过来的部分产业清单,芸香气喘吁吁跑进来,
低声道:“小姐,门房说,有御史台的人递了帖子到前院,说是……要请老爷‘叙话’,
问及府中‘苛待仆役、账目不明’之事!”来了。柳衔枝笔尖一顿。二房的反击,
比她预想的更狠,也更高明——借助外部官场力量施压。若贺镇山被御史盯上,轻则申饬,
重则影响官声前程,整个长房都将陷入被动。“老爷呢?”她问。
“老爷被太夫人叫去松寿堂了,此刻还未回来。”柳衔枝放下笔。看来太夫人也知晓了,
此刻定是在权衡利弊,甚至可能为了尽快平息事端,再次牺牲长房利益。她不能坐等。
“芸香,更衣。我们去松寿堂。”她站起身,目光决然。“小姐,太夫人正在气头上,
您去岂不是……”“正因在气头上,才要去。”柳衔枝对着铜镜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