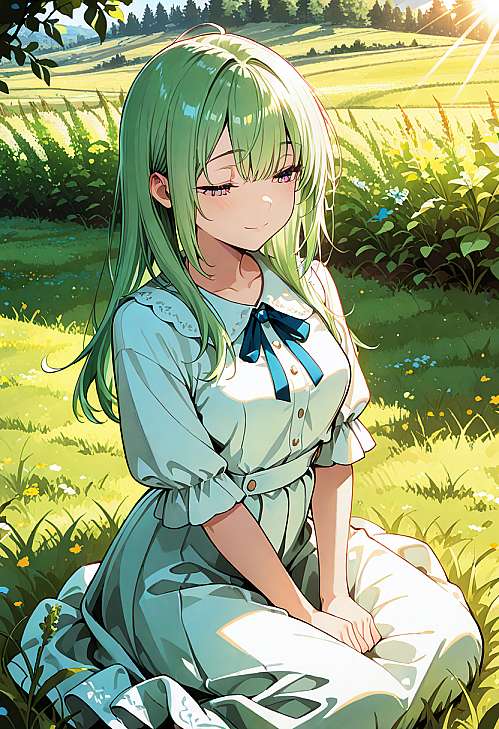日头毒得像后娘的巴掌,王二挺着那个装满了油水的肚子,横在朱漆大门前,鼻孔朝天,
恨不得用下巴看人。“夫人,不是小的不让您进。老爷说了,这几日他在参悟圣人大道,
怕沾了您身上的……煞气。”王二一边说,一边用那双贼溜溜的眼睛往我身后瞄,
确定我那位手握重兵的爹没跟着,腰杆子瞬间又直了三分。“再说了,现在京城里都传遍了,
沈将军这次回京,是凶多吉少。老爷是清流人家,最讲究个洁身自好,您要是识趣,
就别给刘家招灾惹祸。”他这话说得抑扬顿挫,跟唱戏似的,显然是背了好几遍的词儿。
门缝里,隐约能看见一角青色的衣袍,正鬼鬼祟祟地往这边探头。呵。参悟大道?
我看他是在参悟怎么把“软饭硬吃”这门手艺发扬光大吧。我没说话,
只是慢慢解下了腰间那条用牛皮浸了油、又编了金丝的马鞭。王二的脸色变了。
门缝里那角青袍抖了一下。1日头毒辣,晒得青石板路直冒烟。沈千金站在自家府邸门前,
手里提着给夫君带的两坛子好酒,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。眼前这扇朱红大门,
紧闭得像是个守身如玉的烈女。最离谱的是,门上那把铜锁,崭新锃亮,大得像个香瓜,
在阳光下闪烁着“拒人千里”的贼光。她出门不过半月,
回娘家探望那个据说“病入膏肓”实则是吃撑了积食的老爹,怎么回来一看,
这家都快成了别人的了?“开门。”沈千金喊了一声。声音不大,
但透着一股子在军营里练出来的穿透力。门里头静悄悄的,连个喘气的声音都没有,
仿佛里面的人全体飞升成仙了。“刘高义,你给我把门开开!”沈千金提高了嗓门,
手里的酒坛子往地上一墩,发出“咚”的一声闷响。这一声,没震开门,
倒是把门口那两座石狮子震得仿佛都抖了三抖。过了好半晌,
门里才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,紧接着,门房老张那公鸭嗓子隔着厚厚的门板,
怯生生地飘了出来。“夫……夫人?您怎么回来了?”“这是我家,我不回来去哪儿?
去你家过年吗?”沈千金气笑了,抬脚就往门上踹了一脚,“少废话,开门!”“哎哟,
夫人息怒,夫人息怒!”老张在里面急得直跺脚,可就是不听见拔门栓的声音,
“不是小的不开,是……是老爷吩咐了,这几日府里要……要搞什么‘闭关锁国’,不,
是‘闭门清修’,谁也不见!”闭门清修?沈千金看着那把崭新的大铜锁,心里跟明镜似的。
什么清修,这分明是听到了什么风声,以为沈家要倒霉了,急着跟自己划清界限呢。
她这个夫君刘高义,人如其名,眼高手低,满口仁义。平日里自诩是诸葛孔明转世,
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,其实胆子比兔子还小。街上有个卖切糕的瞪他一眼,
他都能回家写三篇《讨贼檄文》,然后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。
这次八成是听说沈老将军被皇上召回京城“问话”,就吓得魂飞魄散,生怕被牵连,
干脆来个闭门不见。“刘高义,你给我听着!”沈千金后退两步,活动了一下手腕,
关节发出咔吧咔吧的脆响。“我数三声。你要是不开门,我就当这门是匈奴的城墙,
今天我就给你演一出‘单骑破关’!”“一!”门里一片死寂。“二!
”隐约听见里面有人喊:“快!快去搬桌子!顶住!顶住!”呵,还真把这儿当战场了?
沈千金冷笑一声,撩起裙摆,露出脚上那双特制的、包了铁皮的快靴。
这可是她当年在边关踢马球用的,一脚下去,连马腿都能踢断,何况这两扇破木板?“三!
”话音未落,沈千金身形一转,借着腰力,一记漂亮的回旋踢,重重地踹在了大门的中缝上。
轰!一声巨响,仿佛平地起了个惊雷。那把威风凛凛的大铜锁,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,
就连着门鼻子一起飞了出去。两扇大门哀嚎着向内敞开,
露出了门后那群正搬着太师椅、花瓶、甚至还有一口咸菜缸的家丁们。
他们保持着搬运的姿势,一个个张大了嘴,像是被施了定身法的蛤蟆。
沈千金拍了拍裙角并不存在的灰尘,跨过门槛,笑得一脸和善。“哟,这是干嘛呢?
知道我回来,特意把家底都搬出来晒太阳?”2家丁们面面相觑,腿肚子直转筋。
他们太清楚这位夫人的手段了。当年老爷纳妾,夫人没哭没闹,只是在院子里立了个靶子,
蒙着眼睛射飞刀,刀刀擦着老爷的头皮过去。第二天,那位小妾就自请去尼姑庵带发修行了,
说是看破了红尘,其实是看破了生死。“夫……夫人……”门房老张哆哆嗦嗦地想上前,
却被一个穿着绸缎长衫、满脸横肉的男人推开了。这人是刘高义新提拔的管家,叫王二。
据说是刘高义的远房表亲,大字不识一个,但拍马屁的功夫炉火纯青,
把刘高义哄得找不着北。王二挺着肚子,手里还捏着把紫砂壶,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。
他虽然也被刚才那一脚吓了一跳,但想到老爷在书房里的“锦囊妙计”,胆气又壮了起来。
“沈氏!你……你竟敢毁坏府门!这可是老爷亲笔题字的门匾下方的门!
你这是对斯文的践踏!对孔孟之道的大不敬!”王二指着沈千金的鼻子,唾沫星子乱飞。
沈千金挑了挑眉。哟,这年头,连狗都学会掉书袋了?“王二,是吧?
”沈千金慢条斯理地往前走了一步,“我记得上个月,你还在后厨偷吃猪头肉,
被我罚了三个月月钱。怎么,这才几天不见,就穿上长衫,装起读书人来了?
”王二脸色一红,随即恼羞成怒。“此一时彼一时!现在老爷让我掌管全府!
你……你现在是戴罪之身的家眷,还敢这么嚣张?老爷说了,沈家犯了大事,
为了不连累刘家的清誉,今日起,这个门,你进不得!”说着,他一挥手,
对着周围的家丁喊道:“都愣着干嘛?给我拦住她!老爷有赏!谁拦住她,赏银十两!
”十两银子,够这些家丁喝一年的酒了。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,
几个新来的、不知道沈千金厉害的愣头青,互相使了个眼色,举着哨棒就围了上来。“夫人,
得罪了!”沈千金叹了口气。她本想以德服人,奈何这些人非要逼她以武服人。
“既然你们这么想要那十两银子,那我就送你们去医馆花个痛快。”话音未落,
沈千金身形一闪。没人看清她是怎么出手的。只听见“啪、啪、啪、啪”四声脆响,
像是过年放的鞭炮。那四个家丁手里的哨棒还举在半空,人已经像陀螺一样原地转了三圈,
然后整整齐齐地捂着脸,倒在了地上。每个人脸上,
都浮现出一个红彤彤、五指分明的巴掌印,肿得像刚出笼的馒头。王二吓傻了。
他手里的紫砂壶“啪”地一声掉在地上,摔得粉碎。“你……你……”沈千金一步步逼近,
脸上带着笑,眼里却没有半点笑意。“王管家,你刚才说,谁进不得这个门?
”“我……我……”王二步步后退,直到后背抵上了那口咸菜缸。“这个家,姓刘,
但这房子,姓沈。”沈千金伸出手,轻轻拍了拍王二那张满是油光的脸,
“这地砖、这柱子、这瓦片,连你刚才摔碎的那把壶,都是本夫人的嫁妆。你拿着我的钱,
吃着我的饭,还想把我关在门外?”“这叫什么?这叫端起碗吃肉,放下筷子骂娘。
”沈千金声音骤然一冷,“跪下!”王二膝盖一软,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,磕头如捣蒜。
“夫人饶命!夫人饶命!是老爷……都是老爷逼我的!”沈千金嫌弃地擦了擦手。
“滚一边去。回头再跟你算账。”她跨过王二,径直往内院走去。她倒要看看,
那位躲在书房里“参悟大道”的刘大才子,到底给她准备了什么惊喜。3穿过垂花门,
沈千金停住了脚步。她记得走之前,这院子里种的是几株西府海棠,开花的时候粉白一片,
甚是好看。可现在,海棠树没了。取而代之的,是一堆奇形怪状的石头,
摆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阵法。中间还挖了个小水坑,里面养了几只半死不活的乌龟。
“这是什么鬼东西?”沈千金指着那堆石头问。跟在后面的丫鬟小翠原来是沈千金的陪嫁,
刚才躲在角落里不敢出来凑了上来,带着哭腔说:“小姐……哦不,夫人。老爷说,
这叫‘玄武镇煞局’。说是……说是您身上杀气太重,克了他的文运,所以要用石头压一压,
再用乌龟……化解一下。”沈千金听得太阳穴直跳。杀气重?克文运?
他刘高义考了八年才中个举人,连进士的毛都没摸着,这也能怪到她头上?
这不是拉不出屎怪茅房没引力吗?正想着,西厢房的帘子一掀,走出来一个女人。
这女人穿着一身素白的长裙,腰身收得极细,走路如弱柳扶风,手里还捏着一方帕子,
捂着心口,一副随时都要晕倒的样子。这是谁?沈千金搜遍了脑海,也没记得家里有这号人。
那女人看到沈千金,先是愣了一下,随即眼圈一红,眼泪说来就来,比水龙头还快。“哎呀,
这便是姐姐吧?”女人走上前,福了一福,声音嗲得能掐出水来,“妹妹柳如烟,见过姐姐。
姐姐这一身……好生威武,倒不像是个女子,倒像是……像是那梁山上的好汉。
”沈千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柳如烟?这名字听着耳熟。哦,想起来了。
红小筑”里那个号称“卖艺不卖身”、弹得一手好琵琶、专门给落魄书生送温暖的清倌人吗?
刘高义以前没少拿私房钱去捧场,还写过几首酸掉牙的诗送给她。怎么?
这是趁着老虎不在家,猴子把戏子领进门了?“谁是你姐姐?”沈千金抱着胳膊,
上下打量了她一眼,“我娘只生了我一个。你这是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,也敢乱认亲戚?
”柳如烟脸色一僵,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“姐姐说笑了。
是刘郎……是老爷怜惜我身世飘零,接我来府上暂住。老爷说了,姐姐出身将门,
性子……直爽,不懂这些文人雅趣。日后便由妹妹陪着老爷红袖添香,
姐姐只管操持家务便是。”红袖添香?沈千金差点笑出声。这算盘打得,
隔着二里地都听见响了。这是想让她当免费保姆,供着这对狗男女风花雪月?“柳姑娘,
你这身衣服,料子不错啊。”沈千金突然换了个话题,伸手摸了摸柳如烟的袖子。
柳如烟得意地挺了挺胸:“这是老爷特意为我选的‘云雾纱’,说是最配我的气质。”“嗯,
是不错。”沈千金点点头,“这是我去年过生日,我爹送来的贡品。我嫌颜色太素,
像披麻戴孝,就扔库房里垫箱底了。没想到,刘高义倒是废物利用,给你穿上了。
”“你……”柳如烟的脸瞬间绿了。“还有这个簪子。”沈千金指了指她头上那根碧玉簪,
“这是我及笄时,太后赏的。你戴着不嫌沉吗?小心压断了脖子。
”柳如烟下意识地捂住了头,退后两步,眼里闪过一丝慌乱。
她原以为沈千金只是个只会舞刀弄枪的粗鄙妇人,没想到嘴巴这么毒。“行了,别演了。
”沈千金拍了拍手,“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些破烂,回头我让人打包送你。不过现在,
你给我让开。我要去见见那位‘刘郎’,问问他这软饭吃得还顺口不。”4书房的门虚掩着。
里面传来刘高义抑扬顿挫的读书声: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
劳其筋骨……”沈千金一脚踹开门。“别苦了,刘高义。你那心志本来就不咋地,
再苦就馊了。”刘高义正坐在书案后,手里捧着本《春秋》,装模作样地摇头晃脑。
见沈千金进来,他并没有表现出惊慌,反而慢慢放下书,露出一种“悲天悯人”的神情。
他长得倒是人模狗样,白面微须,颇有几分儒雅气质,只是那双三角眼破坏了整体美感,
透着一股子算计。“沈氏,你回来了。”他叹了口气,语气沉痛,“你可知,你这一脚,
踹碎的不是门,是我们刘家的脸面,是斯文扫地!”“少跟我扯犊子。
”沈千金拉过一把椅子,大马金刀地坐下,“门锁是怎么回事?
院子里那个唱戏的是怎么回事?还有,我库房里的东西,怎么跑到别人身上去了?
”刘高义站起身,背着手,走到窗前,留给沈千金一个忧郁的背影。“沈氏,你不懂。
如今朝堂局势波谲云诡。你父亲……沈将军,此次回京,怕是难逃一劫。我刘家世代清白,
断不能卷入这种是非之中。”他转过身,目光灼灼地看着沈千金,“我这么做,
也是为了保全大局。至于如烟……她是个苦命人,也是个懂我的人。她能陪我吟诗作对,
能懂我胸中抱负。而你……”他摇了摇头,一脸嫌弃,“你除了舞刀弄枪,懂什么?
你连平仄都分不清,如何做我刘高义的贤内助?”沈千金听乐了。“刘高义,你是不是忘了,
当年你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的时候,是谁给你买的笔墨纸砚?是谁出钱给你捐的官?
是谁帮你打点上下,才让你坐上了这个七品芝麻官的位置?”“现在你跟我谈平仄?谈抱负?
”沈千金站起身,一步步走到他面前,比他还高出半个头。“你的抱负,就是花着老婆的钱,
养着小老婆,然后还嫌老婆没文化?”刘高义被她的气势逼得后退一步,撞在了书案上。
“你……你粗俗!不可理喻!”他涨红了脸,从袖子里掏出一封信,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。
“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,那就别怪我无情。这是休书!你拿着它,回你沈家去吧!
我刘庙小,容不下你这尊大佛!”5休书?沈千金低头看了一眼。字写得倒是不错,
洋洋洒洒,列了她“七出”之罪。
么“无子”其实是他自己不行、“妒忌”指不让他纳妾、“口舌”指骂他废物。
“好。很好。”沈千金拿起那封休书,吹了吹上面未干的墨迹。“刘高义,
这可是你自己写的,别后悔。”刘高义冷哼一声,整理了一下衣领,恢复了那副高傲的模样。
“君子一言,驷马难追。我刘高义做事,从不后悔。你走吧,念在夫妻一场,
你的嫁妆……咳,那些笨重之物,你也带不走,就留在府里,
当作这些年你对我精神折磨的补偿吧。”听听。这是人话吗?休了人,还想吞嫁妆?
沈千金没生气,反而笑了。她笑得花枝乱颤,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“刘高义啊刘高义,
你真是个人才。你这脑子,要是用在治水上,黄河早就倒流了。
”她从怀里掏出一叠厚厚的纸,往桌上一拍。“睁大你的狗眼看看,这是什么?
”刘高义狐疑地凑过去一看,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房契、地契、店铺契约……上面白纸黑字,
写的全是“沈千金”三个字。“这座宅子,是我买的。城东那两个铺子,是我的陪嫁。
就连你身上穿的这件长衫,都是用我的银子做的。”沈千金收起笑容,目光如刀。
“既然你休了我,那咱们就按规矩办。带着你的柳如烟,还有你那些破书,给我滚出去。
现在,立刻,马上。”“你……你敢!”刘高义慌了,“这是我家!我是朝廷命官!
你……你爹马上就要倒台了,你一个罪臣之女,凭什么赶我走?”“谁告诉你我爹要倒台了?
”沈千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,“我爹这次回京,是因为边关大捷,皇上特旨召回,
要封他为‘镇国公’,世袭罔替。”轰!这句话,比刚才踹门那一脚还狠,
直接把刘高义的天灵盖都震飞了。镇……镇国公?那可是超品爵位!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!
刘高义的腿开始打摆子,脸上的高傲瞬间崩塌,变成了一种滑稽的惊恐。“不……不可能!
外面都传……”“传什么?传谣言的那几个人,已经被锦衣卫抓进去喝茶了。怎么,
你也想去尝尝?”沈千金拿起桌上那封休书,在刘高义面前晃了晃。“这休书,我收下了。
刘大人,恭喜你,你自由了。现在,请你圆润地,滚出我的将军府。”6刘高义那张脸,
精彩得像是开了染坊。先是白,白得像刚刷了粉的墙;紧接着是红,
红得像猴子屁股;最后变成了紫,紫得像茄子打了霜。他死死盯着沈千金手里那封休书,
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突然,他动了。这位平日里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读书人,
此刻竟然爆发出了饿狗扑食般的速度。他猛地向前一窜,伸手就去抢那张纸。“娘子!误会!
都是误会!”沈千金早有防备。她脚步轻轻一错,身子往旁边一闪。刘高义扑了个空,
整个人失去了重心,直挺挺地趴在了书案上。那方名贵的端砚被他撞翻了,
黑乎乎的墨汁泼了他一脸,顺着鼻尖往下滴。“误会?”沈千金两根手指夹着休书,
举过头顶,像是举着一道圣旨。“白纸黑字,还盖了你刘大人的私印。你现在告诉我是误会?
怎么,你刚才是被鬼上身了,还是脑子被门夹了?”刘高义顾不上擦脸上的墨汁。
他手忙脚乱地爬起来,脸上堆起了一朵比哭还难看的笑花。“千金……啊不,夫人!贤妻!
”他搓着手,腰弯得像只煮熟的大虾。“为夫……为夫刚才是在试探你!对,是试探!
”“古人云,夫妻本是同林鸟,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我是怕……怕岳父大人升了官,
你嫌弃我官卑职小,所以才故意写这休书,想看看你对我是否真心!
”沈千金听得胃里一阵翻腾。这人不去写话本真是屈才了。这种瞎话,
他是怎么做到张口就来,还脸不红心不跳的?“试探我?”沈千金冷笑一声,
“那这位柳如烟姑娘呢?也是你请来试探我的道具?”站在门口的柳如烟,
此刻已经吓得面无人色。她虽然是个风尘女子,但也知道“镇国公”三个字的分量。
那是能在京城横着走的人物!见沈千金看过来,她腿一软,顺势就往地上倒去,一手扶额,
气若游丝。“哎呀……我……我头好晕……老爷,
我怕是旧疾复发了……”这招“弱柳扶风”,她在怡红小筑用过无数次,百试百灵。
男人见了,没有不心疼的。可惜,今天这屋里,做主的不是男人。“晕了?
”沈千金瞥了她一眼,转头对门外喊道:“小翠!”“奴婢在!”小翠立马跳了出来,
声音洪亮。“去,打一桶井水来。要刚打上来的,越凉越好。柳姑娘既然晕了,
咱们得帮她清醒清醒。这叫‘冷水泼面,起死回生’,是我在军营里学的偏方。
”地上的柳如烟身子一僵。这大秋天的,一桶井水泼下来,不死也得脱层皮。
她“嘤咛”一声,奇迹般地睁开了眼,自己爬了起来。“不……不劳姐姐费心了。
妹妹……妹妹觉得好些了。”7沈千金拉过太师椅,大摇大摆地坐下。
她把那封休书往怀里一揣,然后翘起了二郎腿。“行了,别演了。我这人,最讲道理。
”她指了指刘高义,又指了指柳如烟。“既然休书已写,咱们就是路人。这宅子是我的,
你们住着不合适。给你们半个时辰,收拾东西,滚蛋。”刘高义急了。
他扑通一声跪在沈千金脚边,伸手想去拉她的裙角。“夫人!你不能这样!我是朝廷命官!
你把我赶出去,我住哪儿?这要是传出去,我的官声何在?我的脸面何在?”“你的脸面?
”沈千金一脚把他踹开,“你写休书的时候,想过我的脸面吗?
你让这个女人穿着我的衣服招摇过市的时候,想过我的脸面吗?”“少废话。小翠,点香!
半个时辰后,谁还赖在这儿,就让家丁拿大棒子叉出去!”柳如烟见大势已去,眼珠子一转,
转身就往外溜。“既然姐姐容不下我,那妹妹走就是了。”她走得飞快,
一只手紧紧捂着袖口,另一只手按着头上的发髻。“站住。”沈千金懒洋洋地喊了一声。
“我让你走,没让你带着我的东西走。”柳如烟脚步一顿,回过头,
一脸无辜:“姐姐这是何意?妹妹身无长物,带走的都是自己的贴身衣物。”“贴身衣物?
”沈千金站起身,几步走到她面前。“头上的碧玉簪,摘下来。”柳如烟咬着嘴唇,
不情不愿地拔了下来。“手腕上的羊脂玉镯子,摘下来。”柳如烟眼泪汪汪,
慢吞吞地褪下镯子。“还有……”沈千金目光落在她鼓鼓囊囊的袖口上,“袖子里藏的什么?
拿出来。”柳如烟脸色大变,死死捂住袖口:“没……没什么!这是老爷送我的定情信物!
”“定情信物?”沈千金冷笑一声,一把抓住她的手腕,用力一抖。哗啦啦。
一堆东西掉在了地上。有金瓜子、珍珠耳环、玛瑙手串……甚至还有一个纯金打造的长命锁。
“哟,这长命锁是我满月时候戴的,上面还刻着‘沈’字呢。怎么,你也想改姓沈?
给我当孙子?”沈千金捡起长命锁,吹了吹灰。“小翠,过来搜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