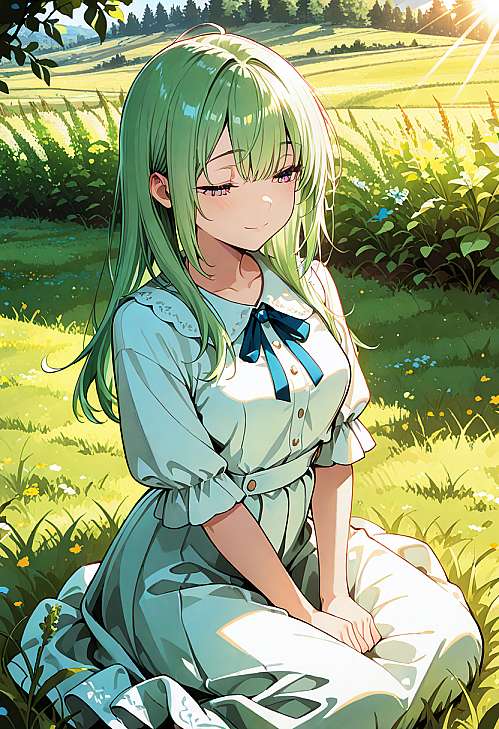我夫君裴衍捡回一头受伤的雪貂,非要当心肝宝贝养着。在侯府,它吃的是天山雪莲,
喝的是晨间甘露,睡的是裴衍的枕边。我不过是说了一句“人畜殊途”,
裴衍就掐着我的脖子,眼神狠戾地说我连只畜生都不如。直到那天,那只雪貂趁我熟睡,
活活咬断了我腹中孩儿的喉管,尖利的牙齿撕开我儿的肚腹,啃食得满嘴是血。
我才终于知道,这只畜生,是他那死去多年的白月光柳莺莺的魂魄附身所变。下一秒,
我猛然睁眼,重生回了裴衍抱着雪貂进门的那一天。他怀里的雪貂,
正用那双看似纯良的眼珠子,怨毒地盯着我。裴衍满眼心疼地安抚着它,
嗓音是我从未听过的温柔,“莺莺别怕,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”我看着他们,笑了。真好。
再过七日,便是皇家秋猎。既然老天爷让我重来一次,那这辈子,你们这对人畜,
就给我锁死,一起下地狱吧。第一章血。漫天的血腥气,浓稠得化不开,
糊住了我的口鼻,让我无法呼吸。我看见我那未足月的孩儿,躺在冰冷的地上,
小小的身体被撕开一个狰狞的口子,肠穿肚烂。一只通体雪白的雪貂,
正埋头在他小小的腹腔里,贪婪地啃食着他的内脏。它抬起头,那张沾满了血污的嘴,
冲着我露出一个酷似人类的、得意的狞笑。“不——!”我凄厉地尖叫,喉咙里涌上腥甜,
猛地从床上坐起。锦被滑落,冷汗浸透了我的中衣,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擂动,
仿佛要挣脱束缚跳出来。窗外,月色如霜,透过雕花木窗洒下一地清辉。不是地牢,
不是那片血泊。是我的卧房。我颤抖着抬起手,抚上自己平坦的小腹。这里,
还没有那个被活活啃食的可怜孩子。我还活着。我重生了。太好了,老天有眼,我回来了。
“吱吱!”一声尖锐的叫声在我耳边响起,带着一丝不耐烦的娇嗔。我僵硬地转过头,
看见了床榻的另一侧,我名媒正娶的夫君,当朝平阳侯世子裴衍。他正侧着身,
将一只雪白伶仃的雪貂搂在怀里,动作轻柔地拍着它的背,仿佛在哄一个受了惊吓的婴孩。
“莺莺乖,不怕,只是个噩梦。”他的声音,是我从未听过的温柔缱绻,
每一个字都像是淬了蜜糖。那只雪貂,就是我梦里那只啃食我孩儿的畜生。
也是他那死去三年的白月光,柳莺莺。它在他怀里拱了拱,一双黑豆似的眼睛,
隔着裴衍的臂弯,怨毒又挑衅地望着我。我浑身的血液,在这一刻瞬间凝固。前世,
就是今天,裴衍从西山围场捡回了这只“通人性”的雪貂。他说它受了伤,可怜,
要养在府里。我那时愚蠢,只当他是一时心善,还亲手为它包扎伤口,喂它食物。
可我不知道,这畜生的身体里,装着的是柳莺莺那颗歹毒的魂。她恨我,恨我嫁给了裴衍,
成了世子妃,占了本该属于她的位置。于是,她用那副无害的畜生皮囊,在我身边为所欲为。
打翻我的安胎药,抓破我的脸,在我有孕时故意从高处跳下,引得裴衍以为是我要害它,
将我狠狠推倒在地,险些流产。而裴衍,每一次都护着它。他会因为我呵斥了它一句,
就罚我跪在雪地里三个时辰。会因为它“受惊”不肯进食,就逼我亲口尝遍所有食物,
证明无毒。甚至在我临盆之际,他守在产房外,怀里抱着的就是这只畜生。我的孩儿出生后,
他更是变本加厉,竟允诺它睡在我们的婚床上。然后,惨剧就发生了。我永远也忘不了,
我抱着孩儿冰冷的尸体,去求裴衍给我一个公道时,他是怎么说的。他一脚将我踹翻在地,
指着我的鼻子骂道:“晏知月!你疯了!莺莺只是一只什么都不懂的畜生!它怎么可能杀人!
分明是你自己没看好孩子,现在竟想污蔑到一个畜生头上!你的心怎么能这么毒!
”我看着他怀里那只瑟瑟发抖,装作惊恐的雪貂。看着他满眼的厌恶与不信。我绝望了。
我笑得癫狂,扑上去想要掐死那只畜生,却被他一掌打得口鼻出血,
命人将我拖进了阴暗潮湿的地牢。在地牢里,我被折磨得不成人形,
最终在无尽的悔恨与怨毒中,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闭眼前,
我听见裴衍对柳莺莺变的雪貂说:“莺莺,别怕,那个毒妇死了,再也没人能伤害你了。
”滔天的恨意,几乎要将我的理智焚烧殆尽。我死死地掐着自己的掌心,
尖锐的刺痛让我瞬间清醒。不能急。这一世,我不会再犯蠢了。裴衍,柳莺莺。
你们不是喜欢人畜情深吗?我成全你们。我会亲手为你们打造一个最华丽的囚笼,
让你们在里面相亲相爱,最后,再一把火,烧得干干净净!“吵醒你了?
”裴衍冰冷的声音响起,不带一丝温度,与他哄那畜生时判若两人。我抬起眼,
对上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,里面是毫不掩饰的疏离与警告。前世的我,
此刻应该会委屈地质问他,为何要将一只畜生带上我们的床。然后,
换来他一句“你连它都不如”的羞辱。但现在,我只是微微牵起嘴角,
露出一个温婉贤淑的笑容。“夫君说笑了,是臣妾自己做了噩梦,与这小东西无关。
”我顿了顿,目光落在雪貂身上,眼神里充满了恰到好处的怜爱与新奇。
“这便是夫君今日救回来的雪貂吗?当真通体雪白,没有一丝杂毛,真是个漂亮的小东西。
”我的反应,显然出乎了裴衍的意料。他眼中的警惕和不耐烦,化为了一丝审视和困惑。
那只雪貂“吱”了一声,似乎也不满我没有像前世那样歇斯底里。
我却仿佛没看见他们的异样,撑着身子坐起来,柔声说道:“夫君,夜里凉,
总抱着它也不是办法。不若让婢女在床边给它搭个暖和的小窝,也让它睡得安稳些。”对,
离我远点,我嫌脏。裴衍沉默地看着我,似乎想从我脸上找出什么破绽。但我没有,
我的脸上只有身为正妻的端庄与大度。良久,他才冷冷地“嗯”了一声,算是同意了。
我立刻扬声唤来婢女,吩咐她们用最柔软的锦缎和狐皮,在床脚搭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小窝。
雪貂被裴衍放进窝里,它似乎有些不甘心,挣扎着想往床上爬。我赶在裴衍发怒前,
轻笑着开口:“这小东西倒是黏人。对了夫君,再过七日便是皇家秋猎,陛下有旨,
各家世子可携带家眷与猎宠同往。这雪貂如此灵巧,带去或许能博得龙颜大悦呢?
”我话音刚落,裴衍的眼睛瞬间亮了。他低头看着那只雪貂,
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骄傲与宠溺,“我的莺莺,自然是最好的。”而那只雪貂,
也得意地挺了挺小胸脯,用头蹭着裴衍的手指。我垂下眼帘,
掩去眸中一闪而过的、冰冷的杀意。皇家秋猎。前世,我就是在秋猎上,被这只畜生设计,
从马上摔下,断了一条腿,成了全京城的笑柄。这一世,就让这盛大的秋猎,
成为你们这对人畜的葬身之地吧。第二章翌日清晨,我醒来时,裴衍已经上朝去了。
床脚的小窝里空空如也,那只名为“莺莺”的雪貂不知所踪。我心知肚明,
定是裴衍将它带去了书房。他的书房,是侯府禁地,除了他自己,连我这个正妻都不得擅入。
前世,他就是这样,将柳莺莺变的雪貂藏在书房,用最好的笔墨纸砚给它当玩具,
甚至亲手为它雕刻玉石磨牙。而我,连给他送一碗参汤,都会被他冷着脸赶出来。
婢女春禾为我梳妆时,忧心忡忡地开口:“夫人,世子爷将那只雪貂看得比眼珠子还重,
您日后可千万别跟它起了冲突,免得……”“我知道。”我淡淡地打断她。镜中的我,
面色平静,眼神却冷如寒潭。“春禾,去库房里,将我那套南海珍珠头面取出来。
”春禾一愣,“夫人,那可是您最珍贵的嫁妆,您不是说要留着重要场合才戴吗?”“今天,
就是重要场合。”我看着镜中的自己,缓缓勾起一抹笑。我要去给婆母,平阳侯夫人请安。
这位侯夫人,出身名门,最是看重规矩与体面。前世,我与裴衍因为雪貂的事屡次争吵,
闹得阖府不宁,她便对我颇有微词,认为我善妒,没有当家主母的气度。这一世,
我要让她亲眼看看,究竟是谁,在败坏侯府的门风。我穿戴整齐,带着春禾,
端着一盅亲手炖的燕窝,往侯夫人的松鹤堂走去。还未进门,
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娇俏的笑声。“母亲,您瞧,衍儿带回来的这只小东西,多有灵性啊!
”是裴衍的妹妹,裴月。我踏进门槛,果然看见裴月正抱着那只雪貂,逗弄着玩。
而我的好夫君裴衍,就坐在一旁,眼神温柔地看着,仿佛在看什么稀世珍宝。
侯夫人坐在主位上,脸上也带着几分笑意,显然对这只雪物很是喜爱。
好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。若不是知道这畜生的真面目,我恐怕也要被这温馨的假象迷惑了。
“知月给母亲请安。”我屈膝行礼,姿态无可挑剔。侯夫人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,
不咸不淡地“嗯”了一声,“起来吧。”裴衍更是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,
全部心神都在那只雪貂身上。我毫不在意,将燕窝奉上,柔声道:“母亲,
这是儿媳亲手为您炖的血燕,您尝尝。”侯夫人接过,用银匙搅了搅,
语气中带着一丝敲打:“你有心了。身为世子妃,就该多在这些事情上用心,
调理好衍儿的饮食起居,为侯府开枝散葉,而不是为了一些小事,整日里愁眉不展。
”来了,又是我善妒,我不懂事。我垂下眼,做出一副虚心受教的模样,
“母亲教训的是,儿媳记下了。”就在这时,那只雪貂忽然从裴月怀里挣脱,
“嗖”地一下窜到了桌上。它直奔那碗血燕而去,伸出粉嫩的舌头就要去舔。“莺莺!
”裴衍低喝一声,却并无多少责备之意。裴月更是夸张地叫道:“哎呀,
这小东西可真是个小馋猫,连母亲的燕窝都敢抢!”侯夫人的眉头,不易察觉地蹙了一下。
前世,我看到这一幕,定会怒不可遏,当场发作,指责一只畜生没规矩。
然后裴衍就会说我小题大做,与一只动物计较,丢了世子妃的体面。但现在,
我只是快步上前,在雪貂的舌头碰到碗沿的前一刻,将燕窝端了起来。雪貂扑了个空,
“吱吱”地叫唤起来,声音里充满了不满。它转过头,一双黑豆眼恶狠狠地瞪着我。
我却不看它,而是转身对着侯夫人,一脸惶恐地跪下。“母亲恕罪!都是儿媳的错,
没有看好这小东西,险些惊扰了您!”我将所有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,姿态放得极低。
侯夫人脸上的不悦,果然缓和了许多。她扶起我,道:“这与你何干?是这小东西顽劣。
”说罢,她看了一眼那只还在“吱吱”乱叫的雪貂,眼神里带上了一丝不喜。裴衍见状,
立刻将雪貂抱进怀里,辩解道:“母亲,莺莺只是顽皮,它没有恶意。”“顽皮?
”我故作惊讶地掩住嘴,声音里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天真与担忧,“夫君,这可不是顽皮。
我听闻,有些灵兽极有灵性,能辨识宝物。它这般扑向血燕,
莫不是……这血燕里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?”我这话,说得极有技巧。
表面上是在为雪貂开脱,夸它有灵性。实际上,却是在暗示——这燕窝,可能有问题。
侯夫人是什么人?后宅浸淫多年,心思玲珑剔配。她立刻就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。她的脸色,
瞬间沉了下去。“来人!”她厉声道,“去把厨房炖燕窝的张妈妈,给我叫过来!”气氛,
一下子紧张起来。裴衍的脸色也变了,他没想到我会来这么一出。他看向我,
眼神里充满了警告。我却回以一个无辜又茫然的眼神。怎么?只许你的心肝宝贝陷害我,
不许我借力打力吗?很快,张妈妈被带了上来,跪在地上瑟瑟发抖。
侯夫人将燕窝往桌上一放,冷冷地问:“这燕窝,是你炖的?
”“是……是老奴炖的……”“里面可有加什么不该加的东西?”“冤枉啊夫人!
老奴就是有天大的胆子,也不敢害您啊!”张妈妈哭喊着磕头。我适时地开口,
声音轻柔:“母亲,想来是儿媳多心了。张妈妈是府里的老人,怎会做这等事。
许是这小东西真的只是贪吃罢了。”我越是这么说,侯夫人心中就越是怀疑。她冷哼一声,
“是不是多心,一验便知。”说罢,她拔下头上的银簪,探入了燕窝之中。
在场所有人的呼吸,都屏住了。片刻后,银簪被拔出。簪身,光亮如初,并无变化。
张妈妈顿时松了一口气,瘫软在地。裴衍的脸色缓和下来,他看向我,眼神里多了一丝嘲讽,
仿佛在说我“多此一举”。那雪貂更是得意,冲着我“吱吱”叫了两声,像是在嘲笑我。
我却笑了。我慢慢地站起身,走到桌边,拿起那支银簪,对着光亮仔细瞧了瞧。然后,
我轻声开口,声音不大,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屋子。“母亲,这簪子……好像不是纯银的。
”侯夫人的笑容,僵在了脸上。第三章侯夫人的脸色,瞬间变得铁青。她最重脸面,
当着儿媳和下人的面,被人指出用了一支成色不足的银簪,
这简直比直接打她的脸还让她难堪。“春禾。”我没有看她,只是淡淡地吩咐道,
“去将我妆匣里那套素银簪子取来,给母亲验验。”“是,夫人。”裴衍的眉头紧紧皱起,
他盯着我,眼神锐利如刀,似乎想要将我看穿。他一定在想,
曾经那个在他面前只会哭闹撒泼的晏知月,怎么会一夜之间,变得如此冷静,
甚至……有些可怕。很快,春禾取来了银簪。我亲手递给侯夫人,柔声道:“母亲,
您再试试。”侯夫人的手有些发抖,她接过银簪,这一次,她没有丝毫犹豫,
狠狠地将簪子插进了燕窝里,搅动了几下。当银簪再次被抽出时,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那原本光洁的银簪,此刻已经变得一片乌黑。燕窝有毒!“啊!”裴月吓得尖叫一声,
失手将怀里的雪貂丢在了地上。雪貂摔得“吱”地惨叫一声,连滚带爬地躲到了裴衍的脚边。
“反了!真是反了!”侯夫人气得浑身发抖,猛地一拍桌子,那碗燕窝被震得翻倒在地,
黑色的汤汁溅得到处都是。“把这个吃里扒外、心肠歹毒的奴才给我拖下去!重打三十大板!
再给我好好审!我倒要看看,是谁指使她的!”张妈妈吓得魂飞魄散,连声哭喊着冤枉,
却还是被两个粗壮的婆子堵住嘴拖了下去。松鹤堂里,一片死寂。侯夫人胸口剧烈地起伏着,
显然是气得不轻。裴衍的脸色也极为难看,他没想到,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他原本以为,
这只是我又一次争风吃醋的拙劣把戏,却不想,竟真的牵扯出了一桩后宅阴私。我垂着眸,
心中一片冰冷。这燕窝,自然是我动的手脚。里面的毒,是一种西域奇花“黑血藤”的汁液,
无色无味,却能慢性损伤人的心脉。前世,侯夫人就是在秋猎后不久,突发心疾而亡。
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她是旧疾复发,无人怀疑。直到我死前,才从两个狱卒的闲聊中得知,
是柳莺莺的远房表哥,买通了张妈妈,在侯夫人的饮食中常年下毒,只为替柳莺莺扫清障碍。
这一世,我便将此事,提前引爆。一来,可以借侯夫人的手,清除府里的内鬼。二来,
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我要让所有人,都对这只雪貂的“灵性”,产生怀疑和恐惧。
我缓缓抬起头,看向裴衍脚边那只瑟瑟发抖的雪貂,
故作后怕地说道:“真是多亏了这只小东西,若不是它通灵性,及时示警,
只怕……只怕母亲今日就要遭了奸人毒手了!”我故意加重了“通灵性”三个字。果然,
侯夫人看向雪貂的眼神,瞬间变了。不再是之前的喜爱,而是带上了一种复杂难言的审视,
甚至……是一丝忌惮。一个能预知危险的畜生?这到底是祥瑞,还是妖物?
裴衍也察觉到了气氛的微妙变化,他立刻将雪貂抱起,沉声道:“母亲,莺莺只是碰巧。
下毒之事,儿子一定会彻查到底,给您一个交代。”他想将雪貂从这件事里摘出去。
我怎么能让他如愿?我幽幽地叹了一口气,语气里充满了担忧:“夫君,话不能这么说。
这小东西如此神异,实在非同寻常。前几日我去城外上香,听闻清虚观的道长说,
近来京中妖气横生,恐有邪物作祟,扰乱家宅安宁。”我顿了顿,目光扫过那只雪貂,
意有所指地继续道:“尤其是这种开了灵智的动物,最容易被不干净的东西附身。
我们侯府是百年世家,最重门楣气运,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啊。”我的话,像一根针,
精准地刺入了侯夫人最敏感的神经。百年世家,门楣气运。这八个字,比她的命还重要。
她看向雪貂的眼神,已经从忌惮,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厌恶和怀疑。“衍儿,
”她的声音冷了下来,“这东西,还是送到别院去养吧,别放在府里了。”“不行!
”裴衍想也不想地拒绝,将雪貂死死地护在怀里,仿佛谁要抢他的命根子。“母亲!
莺莺它不是妖物!它只是通人性而已!”“通人性?”侯夫人冷笑一声,“通人性到能识毒?
衍儿,你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,难道连人畜之别都分不清了吗?为了一个畜生,
你要忤逆我吗?”母子二人,剑拔弩张。这正是我想看到的画面。前世,
裴衍就是用侯夫人的宠爱,作为他肆无忌惮的资本。这一世,我就先斩断他的臂膀。“母亲,
夫君,”我适时地站出来,扮演一个贤良的调解者,“你们别为了这个争吵。
夫君也是爱护小动物,心肠软。母亲也是为了侯府着想,一片慈心。依儿媳看,
不如这样……”我微微一笑,提出了一个谁也无法拒绝的建议。“再过几日便是秋猎,
届时皇家寺庙的大德高僧也会随行,为国祈福。我们不如将这小东西也带上,
请高僧为它看一看,开个光。若它真是祥瑞,那便是我侯府的福气。
若它……若它真有什么不妥,有高僧在,也能及时化解,保我侯府平安。母亲,夫君,
你们看如何?”我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。既给了侯夫人台阶下,也堵死了裴衍的拒绝之路。
他若拒绝,就是心里有鬼,更坐实了这雪貂是妖物的说法。裴衍死死地盯着我,牙关紧咬。
他知道,他落入了我的圈套。但他没有选择。良久,他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:“……好。
”我笑了。柳莺莺,你不是喜欢在人前表演吗?秋猎,就是我为你搭的最大的一个戏台。
到时候,我会请全天下的人,都来欣赏你的“好戏”。我倒要看看,当着天子和高僧的面,
你这只披着畜生皮的孤魂野鬼,还能怎么装!第四章下毒之事,很快就查清了。
张妈妈熬不住大刑,招认了是受人指使,而指使她的人,
正是柳莺莺那位在兵部当差的远房表哥。人证物证俱在,那人很快被下了大狱,秋后问斩。
裴衍为此,被平阳侯叫去书房,狠狠训斥了一顿。一个“治家不严”的罪名,不大不小,
却也足够他灰头土脸一阵子了。他从书房出来后,直接冲进了我的院子。“晏知月!
是不是你!”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,力道大得几乎要将我的骨头捏碎,双目赤红,
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。“是你设计好了一切,对不对?你早就知道燕窝有毒,
故意引莺莺过去,再借母亲的手,将事情闹大!你好深的心机!”我任由他抓着,没有挣扎,
只是抬起眼,平静地看着他。“夫君,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只知道,
若不是莺莺‘示警’,母亲今日就危险了。说起来,它还是我们侯府的功臣呢。”我的平静,
愈发激怒了他。“你还装!”他猛地将我推到墙上,后背撞上冰冷的墙壁,疼得我闷哼一声。
他欺身而上,将我困在他和墙壁之间,呼吸里带着暴怒的气息。“晏知月,我警告你,
不要动莺莺!否则,我让你生不如死!”生不如死?裴衍,你永远也想象不到,
我前世,究竟是怎么生不如死的。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,那张曾让我痴迷了十年的脸,
如今在我眼里,只剩下憎恶。我忽然笑了,笑得凄然又讽刺。“夫君,你这么紧张它,
到底是因为它‘通人性’,还是因为它……像某个人?”裴衍的身体,猛地一僵。
他瞳孔骤缩,死死地盯着我,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。“你……胡说什么!”“我胡说吗?
”我迎着他的目光,一字一句地说道,“柳莺莺。你给它取名‘莺莺’,不就是因为她吗?
你日日将它带在身边,同吃同睡,不也是因为,你觉得它身上,有她的影子吗?”这些话,
像一把尖刀,狠狠地扎进了裴衍最隐秘的心事里。他的脸色,瞬间变得惨白。“闭嘴!
”他怒吼一声,掐着我脖子的手,不自觉地收紧。窒息感传来,我却依旧在笑。“怎么?
被我说中了?裴衍,你真可怜。你不敢承认自己对一个死人念念不忘,
只能将感情寄托在一只畜生身上。你以为这样,就能慰藉你那点可悲的深情吗?
”“我让你闭嘴!”他彻底失控了,手上的力道越来越重。我能感觉到,死亡的阴影,
再次向我笼罩而来。就在我以为自己会再次死在他手上时,门外,
忽然传来侯夫人威严的声音。“衍儿!你在做什么!放开她!”裴衍浑身一震,如梦初醒,
猛地松开了手。我瘫软在地,捂着脖子,剧烈地咳嗽起来。新鲜的空气涌入肺里,
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刺痛。侯夫人快步走进来,看到我脖子上清晰的指痕,
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。“孽子!”她一巴掌,狠狠地甩在了裴衍的脸上。“你疯了吗!
知月是你的妻子,是侯府的世子妃!你竟然为了一个畜生,对她下此毒手!
”裴衍被打得偏过头去,脸上是清晰的五指印。他没有说话,只是死死地攥着拳,
胸口剧烈地起伏。“母亲,”我挣扎着站起来,走到侯夫人身边,声音沙哑地替他“开脱”,
“您别怪夫君,他只是一时情急。都怪我,不该胡言乱语,惹夫君生气。
”我越是表现得大度委屈,侯夫人就越是心疼我,越是恼怒裴衍。她拉着我的手,拍了拍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