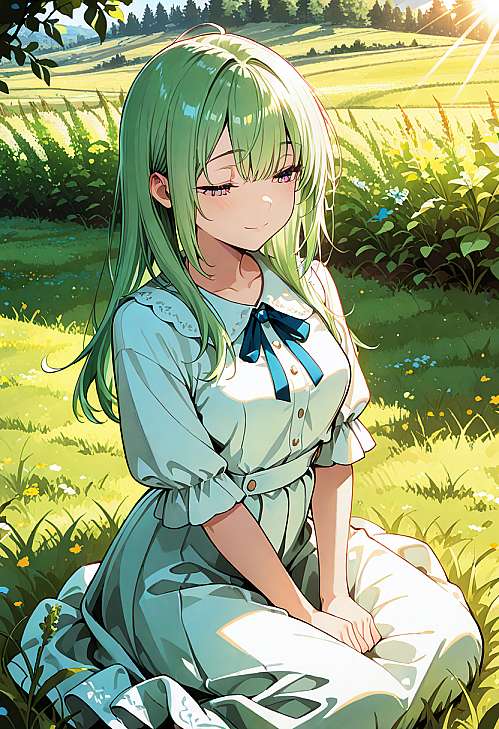第一章 入宫第一天,姐姐们叫我别卷了沈清宜入宫那天,是个晒得人发昏的六月天。
她抱着装衣裳的包袱站在储秀宫门口,后背的汗已经把里衣洇湿了三层。
打从接到圣旨那刻起,她娘就拉着她的手哭成了泪人:“宜儿,宫里水深,你可千万小心,
别叫人害了去!”她爹倒是镇定,捋着胡子说:“无妨,咱家这闺女,谁要害她,
她自己先嫌累。”知女莫若父。沈清宜打小就有一个朴实无华的理想——混吃等死,
寿终正寝。选秀那天,她原本打定主意要落选,特意穿了件洗得发白的旧衫子,
头上只簪了朵绒花。结果太后远远看了她一眼,说:“这丫头瞧着老实。
”她就这么“老实”进了宫,封了答应。此刻她站在储秀宫正堂,
等着拜见这一宫的主位娘娘。
心里已经把最坏的情况设想了一遍:立规矩、跪安、奉茶、听训,
兴许还要被立个下马威——戏文里都是这么唱的。“沈答应是吧?
”一道懒洋洋的声音从帘子后头传出来。沈清宜立刻绷直脊背,
规规矩矩福下身:“嫔妾参见贤妃娘娘。”帘子挑开了。走出来的女子约莫二十出头,
云鬓半偏,簪了支简单的玉兰花簪,身上穿着家常藕荷色衫子,
手里竟还捏着半块没吃完的云片糕。她眼皮都没抬,就近往榻上一歪,
拿帕子擦了擦指尖的糕屑:“站着做什么?坐呀。”沈清宜没敢动。
贤妃终于抬眼瞧了她一下,忽然笑了:“打量我要吃了你?”说着,
扭头朝里间喊了一嗓子:“德妃!你快出来瞧瞧,来了个吓得不敢喘气儿的。
”屏风后头窸窸窣窣一阵响,又走出来一位。这位更是离谱,
手里竟然抱着个绣了一半的猫肚兜,针还插在上头没拔。德妃生得面若银盘,
瞧着就一团和气。她把猫肚兜往榻上一放,上下打量沈清宜,点头道:“嗯,面相周正,
眼神清亮,瞧着不像爱折腾事的。”贤妃接话:“那留下。”沈清宜:?这就……留下了?
她酝酿一路的宫斗防御姿态,像一拳打进棉花里。德妃见她仍站着,索性亲自过来拉她坐下,
又给她手里塞了盏茶:“头回进宫吧?别怕,咱们这宫里没那么多规矩。你是新来的,
往后有什么不懂的,尽管问。用度短了、月例迟了、受委屈了——都来找我。
”贤妃在一旁补充:“找她也行。”沈清宜捧着茶盏,
小心翼翼问:“那……嫔妾每日何时来请安?”“请安?”德妃和贤妃对视一眼,
竟都露出了为难的神色。贤妃先开口:“其实吧,咱们这宫里早年是定的辰时请安。
但你也知道,辰时外头天刚亮,被窝正暖和……”德妃点头:“后来就改巳时。
”“巳时又赶上早膳,边吃边等,点心都凉了。”“所以又改午时。”“午时德妃要午睡。
”德妃轻咳一声:“我那是养神。”贤妃不理她,继续道:“改来改去,咱们索性约定,
有事传话,无事免礼。逢年过节一块儿吃顿饭,平常各自怎么舒坦怎么来。”沈清宜沉默了。
她忽然意识到,娘亲哭了一宿叮嘱她的那些“宫规森严”“步步惊心”,
可能是另一个后宫的传说。德妃见她发愣,以为她担心前程,温声宽慰:“你且安心住下。
侍寝的事也不必着急,轮到了就去,轮不到就当放假。咱们圣上不是那等刻薄人。
”贤妃却忽然想起什么:“对了,说到圣上——”她压低了声音,
神神秘秘凑过来:“前几日贵妃娘娘发话了,今年谁都不许在圣上跟前献殷勤。
冬至宴的歌舞节目,全宫统共报了三个:德妃这边是八名宫女合唱《诗经·关雎》,
德妃你报的?”德妃点头:“上届宫宴排舞,差点没把绣坊的绣娘累死。今年省省力气,
唱几句多省事。”贤妃又道:“丽嫔报了个古琴独奏。”“那另一个呢?
”贤妃面无表情:“丽嫔养的狮子猫报了个翻滚献瑞。”沈清宜一口茶呛进嗓子眼里。
德妃见状,体贴地替她拍背,顺势把那只绣了一半的猫肚兜递给她看:“绣得好不好?
给丽嫔的猫做的,她猫下月过生辰。
”沈清宜看着那肚兜上歪歪扭扭的福字和缺了条腿的麒麟,真诚地夸:“……别致。
”德妃眉开眼笑。贤妃打了个呵欠,从榻上起身:“行了,我先回去了,日头上来发困。
沈答应,你安置吧,缺什么跟底下人说。”德妃也抱着猫肚兜走了。沈清宜独自坐在正堂,
对着窗格子筛下来的细碎日光,发了很久的呆。原来这后宫,
和她听过的戏文——从头到尾都不一样。她推开自己寝间的窗,窗外是储秀宫后院,
几棵老槐树枝繁叶茂,蝉声一阵接一阵。廊下蹲着只狸花猫,正慢条斯理舔爪子。
沈清宜趴在窗沿上,忽然笑了起来。混吃等死?这门差事,她好像来对了。
---第二章 皇后这头衔,烫手山芋没人要沈清宜在后宫的头半个月,
把过去十八年缺的觉全补回来了。没人催她晨起,没人罚她抄经,
连传说中动辄赏一丈红的掌事姑姑都没有——德妃宫里的掌事姑姑姓方,五十来岁,
面相和善,每日见了她都要问:“沈答应,午膳想用些什么?膳房今日进的新鲜鲈鱼。
”沈清宜起初还战战兢兢,怕这是笑里藏刀。半个月后,她已经能面不改色地点单:“清蒸,
多放葱丝,少搁姜。”这日子,别说宫斗了,她连斗字的笔画都快忘了。直到这日午后,
丽嫔抱着狮子猫来串门。丽嫔是去年入宫的,生得娇小玲珑,一张娃娃脸,
说话声音软糯糯的。她那只猫通身雪白,名叫“雪球”,确实会翻滚献瑞——用丽嫔的话说,
练了小半年。沈清宜给她奉茶,丽嫔接过茶盏,却不喝,只是欲言又止地看着她。“沈答应,
”丽嫔压低声音,“你可曾想过……往后往高处走?”沈清宜心里咯噔一下。来了。
果然还是要争的。她这些天太松懈了,竟忘了后宫的本质。
她正斟酌着要怎么谦逊又不失体面地表明自己毫无野心,丽嫔已经凑得更近,
几乎是咬着耳朵:“我是说——万一哪天,圣上要立后。”沈清宜一愣。
丽嫔神色郑重:“万一那不幸之事落到你头上,你可千万要撑住。”不幸之事?
沈清宜张了张嘴:“立后……是不幸之事?”“当然是!”丽嫔瞪圆了眼,
仿佛她说的是什么大逆不道的傻话,“皇后是什么?是后宫之主,是六宫表率,
是每年冬至要率命妇去太庙磕头磕到膝盖淤青的苦差事!
”她掰着手指数:“初一十五率众祭拜,凤印要管,宫务要理,各宫份例要对账,
逢年过节要赐宴,命妇入宫要接见,太后凤体违和要侍疾。你病了有人替你当皇后吗?没有。
你累了有人替你当皇后吗?没有。劳心劳力还落不着好,
有点差池满朝文武都要参你——”丽嫔深吸一口气:“你说,这不是不幸是什么?
”沈清宜听得一愣一愣。正说着,帘子一挑,
德妃、贤妃、还有一位从未见过的雍容女子一同进来。那女子身量高挑,眉目英气,
发髻上只簪一支碧玉棱花簪,通身气派却不怒自威。丽嫔慌忙起身:“贵妃娘娘。
”贵妃摆摆手,示意不必多礼,自己在靠窗的椅上坐下。沈清宜也起身见礼,
心里暗暗惊讶:这就是那位传说中“下令不许献殷勤”的贵妃?贵妃看向她,
倒是先开口:“沈答应?听说你入宫半月,没往御前凑过一步。
”沈清宜老实答:“嫔妾……不认识路。”贵妃唇角微动,像是笑了一下。
贤妃接过话头:“方才丽嫔跟你念叨什么呢?远远就见她神神叨叨的。”丽嫔嗫嚅着不敢答。
贵妃却替她说了:“无非是怕新来的年轻孩子想不开,往那火坑里跳。”火坑。
说的是皇后的位子。贤妃叹了口气,罕见地露出几分惆怅:“说起来,中宫空悬三年,
朝中催立的折子一封接一封。圣上虽压着,恐怕也压不了太久。”德妃低头抚着袖口绣花,
难得沉默。贵妃望着窗外,语气淡得像在说今日天气:“当年先皇后在时,
我曾见她熬油似的熬自己。凤体本就孱弱,还要撑着理事,腊月里发着高热去太庙行礼,
回来躺了三个月。临终前拉着我的手,只说了一句话——”她顿了顿。“‘这个位子,
谁爱坐谁坐,反正我不坐了。’”满室寂静。丽嫔把雪球抱得更紧些,眼眶竟有些红。
贤妃清了清嗓子,强笑道:“好了好了,大好的日子,不说这些。
横竖咱们都一条心——往后谁被点了这个名,咱们集体去替她求情。”德妃点头:“轮流跪。
”贵妃淡淡道:“我不跪。我腰不好。”贤妃瞪她:“你这时候腰倒不好了?
”贵妃理直气壮:“我腰是陈年旧疾,太后都知道。”沈清宜坐在角落里,
看着这几位位高权重的后妃你一言我一语,竟像是在商量如何逃避兵役。她忽然有些明白了。
不是她们无能,是她们太清醒。清醒地知道那个位子意味着什么,
清醒地知道风光背后要拿什么来换。三年了,中宫空悬,不是没人能坐,是没人想坐。
这后宫,不是战场。是避难所。贵妃起身告辞,经过沈清宜身边时,脚步微顿。“你很好。
”她说,“就照这样,一直别变。”沈清宜怔怔点头。贵妃已掀帘去了。
---第三章 皇上来了,全员影后上线摆烂的日子,在入宫第二个月遭遇了第一次危机。
这日午后,沈清宜正和德妃、贤妃、丽嫔在储秀宫后院的槐树下头打叶子牌。
这是德妃新张罗的消遣,说是怕成日闲着把脑子闲坏了。沈清宜连输三局,
正攥着最后几张牌冥思苦想,忽听前头通传的太监连滚带爬奔进来:“圣——圣上驾到!
”那声“到”还没落地,整个后院就跟炸了锅似的。德妃“蹭”地起身,手里的牌撒了一地,
慌忙去够自己搭在椅背上的外衫——她嫌热,早把大衣裳脱了,只穿着件薄绸中衣。
贤妃动作更快,一把将鬓边簪的那朵新鲜栀子花扯下来往袖子里塞,想了想觉得不妥,
又飞快地塞进石凳底下的缝隙里。丽嫔抱着雪球就要往里屋跑,跑了两步又折回来,
把石桌上吃到一半的桂花糖藕端起来塞给宫女。沈清宜握着牌,看呆了。“还愣着做什么!
”贤妃低声喝她,“快装病!”装病?沈清宜还没反应过来,已被德妃一把摁回椅子上。
德妃顺手把自己搭着的披帛扯下来盖在她膝上,又飞快地把自己鬓角揉乱两缕,
往沈清宜身边一歪,摆出一副“我正在探病”的凝重表情。贤妃立在她二人身侧,神色忧戚。
丽嫔蹲在后头,把雪球举在身前做掩护,努力缩小存在感。沈清宜:???
她什么都没来得及问,那道明黄色的身影已经进了后院门。皇帝今年二十有七,
生得清隽儒雅,眉目间有种淡淡的疲倦。他负手站在月亮门下,
扫了一眼满院子兵荒马乱后强行摆出的岁月静好,沉默片刻:“……朕来得不巧?
”德妃率先行礼,声调四平八稳:“圣上驾到,臣妾有失远迎。适才沈答应略感不适,
臣妾正陪她在此歇息。”说着,温柔地看了沈清宜一眼。沈清宜被迫靠着椅背,面色红润,
眼神茫然。皇帝看她一眼:“沈答应不适?”沈清宜干巴巴地:“呃……是,臣妾头晕。
”“传太医了吗?”“传了,”德妃接话,“太医说无大碍,将养几日便好。
”贤妃在一旁补充:“沈答应这是积劳成疾。”沈清宜入宫一月,每日睡到日上三竿,
午膳要吃两碗饭,夜里还要加一餐宵夜。皇帝没说话。
他又看向贤妃:“贤妃鬓边怎么有片叶子?”贤妃面色不改,抬手一摸,
果然从发髻里摸出半片碎叶。她面不改色地拈在指间,温婉一笑:“回圣上,
臣妾方才修剪花枝,未曾仔细梳整。”皇帝又看丽嫔。丽嫔把雪球举高了些,
小声说:“臣妾……在遛猫。”雪球适时地“喵”了一声。皇帝不说话了。
他背着手站了片刻,忽然道:“朕近日在看群臣奏章,又有数本请立中宫的折子。
”话音落地,院子里静得落针可闻。沈清宜分明感觉到,德妃搭在她腕间的手紧了紧。
皇帝的目光缓缓扫过众人:“诸位爱妃有何见解?”没有人说话。德妃低头抚着披帛穗子。
贤妃望着地面出神,仿佛地砖的花纹格外引人入胜。丽嫔把脸埋进雪球的长毛里,
只露出两只泛红的耳尖。皇帝看向沈清宜——这位新入宫、还没有被“污染”的年轻妃子,
或许能说句公道话。沈清宜感受到那道目光,心里警铃大作。她张了张嘴,忽然捂住额头,
声音虚弱:“臣妾……头晕。”说着,往椅背上一歪,闭紧了眼睛。
皇帝:“…………”德妃立刻配合:“圣上,沈答应身子不适,不若臣妾先扶她回房歇息?
”贤妃已经上前一步搭手。丽嫔抱着雪球挪过来,用猫挡住脸。皇帝站在当地,
看着这群妃子你搀我扶,配合默契地往屋里撤退,愣是没人回头看他一眼。
他忽然开口:“贵妃呢?”德妃脚步一顿:“回圣上,贵妃娘娘说今儿个腰疾复发,
正在宫中静养。”“太医看了?”“看了。说需卧床七日,不可劳神。”皇帝沉默良久。
他当然知道贵妃没有腰疾。三年前先皇后薨逝,他有意册立贵妃为后,话才说半句,
贵妃当场跪下,声泪俱下说自己自幼腰肌孱弱,太医断言若操劳过度恐致瘫痪,
实在难当重任。那之后,“腰疾复发”就成了贵妃避之不及时的万能借口。
他不也忍了三年么。皇帝望着面前这群如临大敌的妃嫔,忽然叹了口气。“都别躲了。
”他声音里带着三分无奈,三分疲惫,还有几分连自己都没察觉的委屈。“朕又没说要点谁。
”德妃等人停住脚,面面相觑。皇帝走近两步,在石凳上坐下。他垂着眼,
看着石桌上一片狼藉的叶子牌,沉默半晌,低声道:“朕只是……不知该怎么办。
”这语气不像一国之君,倒像被同僚排挤的倒霉主事。德妃心软了。她松开沈清宜的胳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