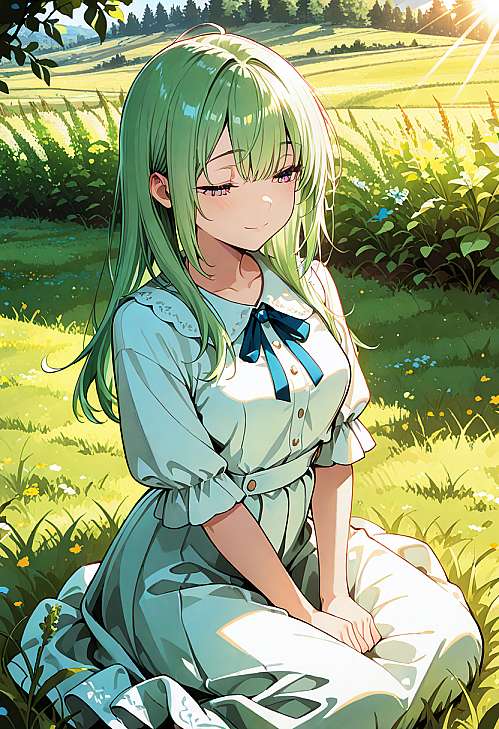我嫁进丞相府第一天,就认清了一件事。这府里敬我的,不是我,
是我头上那顶“相爷夫人”的名头。老夫人叫我“好孩子”,转头就让长孙替相爷管家,
半点权都不肯给我。我不哭不闹,只在夜里把发簪攥得生疼。我贪生怕死,我要的不是体面,
是活下去的路。01红烛烧了一夜。天亮时,喜床上只有我一个人。身边的位置是冷的,
被褥平整,没有一丝褶皱。五十岁的当朝丞相裴文远,昨夜并未踏足新房。我叫沈月华,
十七岁,裴文远续弦的继室。一个出身破落书香门第,用来点缀相府门楣的摆设。
侍女春桃为我梳妆,手都在抖。她小声说:“夫人,
相爷他……”我看着铜镜里那张尚显稚嫩的脸,眼神平静。“相爷国事繁忙,不必多言。
”春桃不敢再说话。梳妆完毕,要去给老夫人请安。裴府的老夫人,是相爷的生母,
七十高龄,精神矍铄。她坐在上首,手里捻着一串佛珠。我恭敬地跪下,奉茶。“母亲,
请用茶。”老夫人没接,目光落在我身上,审视着。良久,她才缓缓开口:“是个好孩子,
起来吧。”声音温和,却带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威严。我依言起身,垂手立在一旁。
老夫人这才端起茶碗,用碗盖撇了撇浮沫,却没有喝。她放下茶碗,发出了清脆的一声响。
“月华,你年纪小,府里的事又杂。往后,这管家之权,就还由修儿暂代吧。”修儿,
是相爷的长孙,裴修。今年二十有二,比我还大五岁。我眼皮都没抬一下,
温顺地应下:“是,全凭母亲做主。”站在老夫人身后的裴修,朝我投来一瞥。
那目光里没什么情绪,像是在看一件器物。我懂。在这座府里,我沈月华,就是一件器物。
老夫人似乎对我的顺从很满意,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她招手让我近前,拉着我的手,拍了拍。
“你刚进门,先好好调养身子,早日为相爷开枝散叶,才是正经事。
”她从腕上褪下一只成色极好的玉镯,戴在我手上。“这是我们裴家的东西,你既是主母,
就该有主母的样子。”镯子入手冰凉,像一道枷锁。我笑着谢恩:“谢母亲赏。
”从老夫人的院子出来,裴修与我走了一段路。他始终在我身后半步,不远不近。“夫人。
”他忽然开口。我停下脚步,回头看他。他比我高出一个头还多,身姿挺拔,
眉眼间有股读书人的清俊,也有久居上位的疏离。“府中诸事,若有需要,
可随时派人来前院寻我。”他说得客气,却是在划定界限。前院是他的地盘,后宅,
暂时还没有我的位置。我微微一笑:“有劳大公子。”他口称“夫人”,
我便叫他“大公子”。我们之间,隔着辈分,也隔着天堑。
回到我那座名为“静安苑”的院子,关上门,我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。
春桃愤愤不平:“夫人,您才是主母!哪有长孙管家的道理?老夫人这也太偏心了!
”我走到梳妆台前坐下,取下头上的金步摇。步摇上的流苏冰冷,硌得我手心发凉。“偏心?
”我自语道,“不,这不是偏心,是规矩。”是裴家立给我看的规矩。我是继室,是外人。
裴修是长孙,是嫡系。这座府,姓裴,不姓沈。春桃还想说什么,被我一个眼神制止了。
“把这些首饰都收起来吧,往后不必戴得如此招摇。”“是,夫人。”夜里,
我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床上。偌大的静安苑,静得能听到风吹过树叶的声音。我睡不着。
我从枕下摸出一支发簪,是母亲留给我的遗物,一支最普通的银簪。
簪尖已经被我磨得有些锋利。我把它紧紧攥在手心,冰冷的簪尖刺得掌心生疼。这点疼痛,
让我无比清醒。我不哭,也不闹。因为我知道,眼泪是这世上最没用的东西。体面,尊严,
在活下去面前,一文不值。我沈月华,贪生怕死。我要的,是走出一条活路。在这相府里,
女人唯一的活路,就是孩子。一个属于我自己的,流着裴家血脉的孩子。我坐起身,
看着窗外的一弯残月。裴文远已经五十岁了。他精力不济,又常年忙于朝政。我不能等,
不能等他偶尔想起,才来我这里。我必须主动。我起身,走到衣柜前,选了一件素雅的寝衣。
又让春桃去小厨房,炖了一盅安神汤。春桃不解:“夫人,夜深了,
您要……”“相爷在书房。”我只说了这四个字。春桃瞬间明白了,脸上闪过一丝屈辱,
但还是低头去了。半个时辰后,我亲自端着那盅汤,走出了静安苑。夜凉如水。
通往书房的路,很长,很静。守门的下人看到我,愣了一下,想通报。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,
轻声说:“相爷累了,我送碗安神汤,不必惊动。”他们不敢拦我。我推开书房的门,
走了进去。裴文远正坐在案后,蹙眉看着一份公文,鬓角已经有了白霜。烛光下,
他的脸显得格外疲惫。他听到动静,抬起头,看到是我,眼中闪过一丝讶异。
我将汤盅放在他手边,声音放得很轻,很柔。“相爷,夜深了,喝碗安神汤,早些歇息吧。
”他看着我,没说话。那眼神,像是在审视一件陌生的物品。02裴文远没有喝那碗汤。
他只是看着我,目光深沉,仿佛要穿透我的皮囊,看到我的骨头里去。“你,想要什么?
”他问得很直接,像是在审问一个犯人。我垂下眼帘,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眼中的情绪。
“月华既已嫁给相爷,便是相爷的人。月华想要的,不过是侍奉相爷,为您分忧。
”话说得滴水不漏。裴文远忽然笑了,笑声里带着一丝苍凉的嘲讽。“分忧?这满府的人,
哪个不是想从我身上得到些什么。”他站起身,走到我面前。他很高,我需要仰视他。
一股淡淡的药草味混杂着墨香传来,那是属于一个老人的味道。“你很聪明,也很大胆。
”他说。我没有接话,只是更深地低下头。他伸出手,捏住我的下巴,迫使我抬头看他。
他的手指粗糙,带着常年握笔的薄茧。“可惜,聪明和大胆,有时候会招来祸事。
”我的心跳漏了一拍,但脸上依旧是那副温顺恭敬的模样。“月华愚钝,不懂相爷的意思。
”他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,久到我几乎要撑不住。然后,他松开了手。“回去吧。
”他转身走回书案,重新坐下,拿起公文。仿佛我从未出现过。我屈膝行了一礼,
端起那碗没动过的汤,默默退了出去。回到静安苑,春桃焦急地迎上来。“夫人,怎么样?
”我将汤盅递给她,摇了摇头。春-桃的脸瞬间白了。我却笑了。“怕什么。
”裴文远没有当场发作,没有训斥我,就说明我还有机会。他那样的人,见惯了逢迎,
也见惯了索取。我的这点心思,在他眼里,或许就像小孩子玩过家家。他不屑,也懒得计较。
这就够了。从那天起,我每日都亲自炖汤,送到书房。有时是安神的,有时是补气的。
裴文远从不喝,也从不说破。我送去,他便让我放下。我离开,他便继续处理公文。
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。府里的下人渐渐看出了门道。他们不敢再明着怠慢我,
但背地里的议论却从未停止。说我这个新夫人,为了争宠,脸面都不要了。我不在乎。
脸面能当饭吃吗?能让我在这个吃人的地方活下去吗?一个月后的一天,我照例去送汤。
推开门,却看到裴修也在。他正站在书案前,与裴文远讨论着什么。看到我进来,
父子俩的谈话停住了。裴修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托盘上,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一下。
我像没看见一样,照常把汤盅放下。“相爷,该歇息了。”裴文远“嗯”了一声。
裴修却开口了,语气很淡:“夫人费心了。祖父的饮食,自有府医和下人照料。
”这是在警告我,不要越界。我转向他,微微一笑。“大公子说的是。只是为人妻者,
为夫君洗手作羹汤,也是分内之事。府医的药方再好,终究是药。我这碗汤,是心意。
”我把“为人妻者”四个字,咬得格外清晰。裴修的脸色沉了下去。我却不再看他,
只对裴文远福了福身。“相爷,月华不打扰您和……大公子议事了。
”我故意在“大公子”三个字上停顿了一下,才转身离开。我能感觉到,
身后那道冷厉的目光,几乎要把我的背灼穿。走出书房,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这是我第一次,正面迎击裴修。我必须让他,让这府里所有人都明白。就算我没有管家权,
就算我是个摆设。我也是丞相明媒正娶的夫人。是裴修名义上的祖母。这个身份,
是我唯一的依仗。那天晚上,裴文远第一次踏进了静安苑。他来的时候,我正准备就寝。
没有预兆,也没有通传,他就那么站在了门口。春桃吓得跪在地上。
我心里也掀起了滔天巨浪,面上却极力保持镇定。我走上前,为他宽衣。
“相爷……”他抓住我的手,力气很大。“你今天,是故意的。”是陈述句,不是疑问句。
我知道他在说书房的事。我点点头,没有否认。“是。”他眼中的审视意味更浓了。
“为什么?”“因为月华是您的夫人。”我抬起头,直视着他的眼睛,
“月华可以没有管家权,可以被下人议论,但绝不能容忍有人质疑我对您的心意,
哪怕是……大-公子。”我再一次,把那三个字说得意味深长。裴文远沉默了。许久,
他松开了我的手,坐在了床边。他看着屋里的陈设,忽然问:“住得还习惯吗?”“习惯。
”“下人可有怠慢?”“没有。”他点点头,神情有些疲惫。“睡吧。”说完,
他便和衣躺下,背对着我。我知道,他不会碰我。但他留下了。这就是我的胜利。
我吹熄蜡烛,在他身边躺下,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。黑暗中,
我能听到他沉稳但略显苍老的呼吸声。我的心,也前所未有地安定下来。只要他肯来,
我就有希望。第二天一早,相爷在静安苑过夜的消息,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整个府邸。
我去给老夫人请安时,她的脸色不算好看。裴修也在,看我的眼神,冷得像冰。我不在乎。
两个月后,府医来请脉,诊出了喜讯。我怀孕了。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裴文远时,
他正在练字。他握着笔的手,停顿了一下。墨汁滴落在宣纸上,晕开一团小小的墨迹。
他没有回头,只是淡淡地问:“确定了?”“是,府医说,已经快两个月了。
”他又沉默了很久,才放下笔。“知道了。好好养着吧。”他的反应,
比我想象中要平淡得多。可我知道,从这一刻起,一切都不一样了。
我终于在这座吃人的相府里,扎下了我的第一条根。03怀孕的消息,
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,在裴府激起了层层涟漪。最先有反应的是老夫人。
她把我叫到跟前,拉着我的手,脸上是掩不住的笑意。“好孩子,好孩子,
你可真是我们裴家的大功臣。”她当即吩咐下去,给我院里添了两个经验丰富的婆子,
四个机灵的丫鬟。又把库房里最好的补品,流水似的往我这里送。那份热络,
与我刚进门时判若两人。我知道,她看重的不是我,是我肚子里的这块肉。裴文远唯一的,
嫡出的血脉。裴修和他父亲,都是裴文远与原配所生。裴文远的另外几个儿子,皆是庶出,
早已分府另过。我肚子里这个,若是儿子,便是相府名正言顺的嫡子。分量,自然不同。
裴修来看过我一次。他站在院子里,隔着珠帘,没有进来。“祖母身子要紧,府中诸事,
就不来烦扰了。”话说得客气,疏离感却更重了。我隔着帘子,能看到他模糊的身影。
“有劳大公子挂心。”他站了一会儿,便转身走了。我能感觉到,我的存在,
让他感到了威胁。这种威胁,随着我肚子的日益隆起,变得越来越清晰。怀孕初期,
我的孕吐反应很严重。吃什么吐什么,整个人瘦了一圈。老夫人派来的张婆子,
每日端来一碗黑漆漆的安胎药。那药苦得发涩,闻着就想吐。我每次都屏住呼吸,
一口气喝完。春桃看着心疼:“夫人,这药也太苦了,不然跟老夫人说说,换个方子?
”我摇摇头。这不是药苦不苦的问题。这是老夫人的“关心”,我不能拒绝。喝了半个月,
我的孕吐不仅没好,反而更严重了。有一次,我甚至吐出了血丝。春桃吓坏了,
哭着要去请府医。我拦住了她。我躺在床上,浑身发冷,脑子却异常清醒。这药有问题。
我让春桃悄悄把药渣收起来。然后,我借口想吃城南一品斋的点心,打发张婆子出府去买。
张婆子一走,我立刻让春桃拿着我的名帖,从后门出去,去请宫里的王太医。
王太医是裴文远的亲信,只听他一人的。用我的名帖去请,老夫人和裴修就算知道了,
也说不出什么。王太医来得很快。他为我诊了脉,又看了药渣,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“夫人,
这方子里,多了一味牵机草。”我心中一凛。牵机草,少量可活血,量大,则会动了胎气。
日积月累,足以让我悄无声息地滑胎。好狠的手段。我看着王太医,轻声问:“太医,
您看这事……”王太医是聪明人,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。“回夫人,此乃小事一桩。
是开方子的府医学艺不精,错用了药材。待老臣去训斥他一番,重开一副温和的方子即可。
”他把事情揽在了府医身上,摘清了所有人。我知道,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。我没有证据,
闹大了,只会说我小题大做,甚至会反咬我一口,说我容不下府里的人。“有劳王太"医了。
”王太医走后,我靠在软枕上,出了一身冷汗。是谁?是看不惯我得宠的老夫人?
还是视我为威胁的裴修?又或者是,这府里某个不起眼的下人,受了谁的指使?我不知道。
但我知道,从今天起,我不能再任人拿捏。我的孩子,我要自己护着。傍晚,张婆子回来了。
我屏退了所有人,只留下她一个。我看着她,把王太医重开的方子放在桌上。“张婆子,
你来我院里,有一个月了吧?”张婆子有些不安,点点头:“是,夫人。”“我待你如何?
”“夫人仁慈,待下人们都很好。”我笑了笑,拿起那张方子。“王太医说,
之前的方子不对,府医错用了一味药。从今天起,就按这个方子抓药吧。
”张婆子的脸白了一下,眼神闪躲。“是,老奴知道了。”我端起茶杯,轻轻吹了口气。
“张婆子,我这个人,向来恩怨分明。谁对我好,我记在心里。
谁若是想害我……和我的孩子……”我顿了顿,抬眼看她,目光冰冷。“我拼了这条命,
也绝不会放过他。”张婆子“扑通”一声跪下了,浑身抖得像筛糠。“夫人饶命!夫人饶命!
老奴什么都不知道啊!”我看着她,没说话。我知道,她背后一定有人。但现在,
我还不能动她。我需要她去传话。告诉她背后的人,我沈月华,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
想要动我的孩子,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。从那以后,我院里的饮食汤药,
都由春桃亲手经管。所有入口的东西,必须用银针试过。我变得格外小心,
像一只护食的母兽,警惕着周围的一切。裴文远来看我的次数多了些。他会坐一会儿,
问问我的身体,看看我日渐隆起的肚子。话不多,但他的出现,本身就是一种表态。
他是在告诉府里的人,这个孩子,他在意。有了他的庇护,我的日子好过了很多。十月怀胎,
一朝分娩。那日,我疼了一天一夜,几乎去了半条命。终于在黎明时分,生下了一个男孩。
孩子哭声洪亮。我听着那哭声,也跟着流下泪来。我知道,我在这相府的第二条根,
也稳稳地扎下了。孩子被抱出去,府里一片欢腾。裴文远亲自为他取名,裴允。允,应允,
应许。是上天应许给他的,一个嫡子。04允哥儿的出生,
让我在裴府的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。我不再是那个可有可无的摆设。我是相爷嫡子的生母,
沈夫人。来我院里请安、巴结的人多了起来。送来的贺礼,在库房里堆成了小山。
老夫人抱着允哥儿,笑得合不拢嘴,赏了我许多贵重东西。裴文远也日日都来看我们母子。
他抱着小小的、软软的允哥儿,那张一向严肃的脸上,会露出难得的温情。只有裴修,
依旧淡淡的。他来看过一次,送了份厚礼,说了几句场面话,便走了。我知道,
我们之间的那道墙,更高了。允哥儿满月那天,府里大宴宾客。我抱着孩子,
坐在裴文远身边,接受着众人的祝贺。席间,裴文远当众宣布,将城郊的一座温泉庄子,
记在了允哥儿名下。那座庄子,是原配夫人的嫁妆,一直由裴修打理。如今,裴文远一句话,
就给了允哥儿。所有人都看向裴修。他端着酒杯,脸上没什么表情,只是对裴文远举了举杯。
“孙儿替允弟,谢祖父赏。”风度翩翩,滴水不漏。可我知道,这等于是在他心上剜了一刀。
宴席散后,我回到院里。我让奶娘把允哥儿抱下去,自己坐在灯下,开始看账本。这些账本,
是我院里这个月的开销。自从怀孕后,老夫人便把静安苑的管理权给了我。地方不大,
账目却不少。我看得仔细,一笔一笔地核对。春桃走进来,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。“夫人,
这是大公子派人送来的。”我打开盒子,里面是那座温泉庄子的地契和账册。做得干净漂亮。
我合上盒子,放在一边。“春桃,去把刘婆子叫来。”刘婆子是府里的老人,管着采买。
之前因为我怀孕,没少在我这里捞油水。刘婆子很快来了,一脸谄媚的笑。“夫人,
您叫老奴来,有什么吩咐?”我把院里的账本推到她面前。“刘婆子,你看看。这个月,
院里采买燕窝,花了八十两。可我记得,我吃的官燕,市价不过五十两一斤。
这多出来的三十两,是花在哪儿了?”刘婆子的冷汗“唰”地就下来了。
“这……这……夫人,许是……是记错了……”“记错了?”我冷笑一声,“还有这木炭,
用的是次等烟炭,报的却是上等银骨炭的价。刘婆子,你当我是傻子吗?
”我把账本狠狠地摔在地上。刘婆子吓得直接跪下了。“夫人饶命!夫人饶命!
是老奴一时糊涂!”院里的下人都被惊动了,围在门口,大气不敢出。我就是要让他们看。
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,我沈月华,不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新夫人。“糊涂?”我站起身,
走到她面前,“你在我这里,一个月就多拿了近百两。这府里上上下下多少主子,
你又捞了多少?”“你这是在挖裴家的根!”刘婆子磕头如捣蒜:“老奴再也不敢了!
求夫人看在老奴伺候府里多年的份上,饶了老奴这次吧!”“饶了你?”我慢慢地踱步,
“府有府规。你这样的刁奴,不严惩,如何能服众?”我看向门口的管事。“来人,
把她拉下去,打二十板子,赶出府去!她这些年贪的,一五一十给我追回来!
”管事愣了一下。二十板-子,足以要了这个婆子半条命。他看向我,眼神里有些犹豫。
我知道,他是在等。等老夫人,或是大公子那边来人。毕竟,刘婆子是府里的老人,
关系盘根错节。我没说话,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院子里,一片死寂。就在这时,
门口传来一个声音。“夫人何必发这么大火。”是裴修。他走了进来,身后跟着几个管事。
他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刘婆子,又看向我。“一个下人,交给管事们处置就是了。
夫人刚出月子,该好生歇着。”他这是来保刘婆子了。我心里冷笑。我就知道,
这府里的采买,油水最足,必然是他的人。我动刘婆子,就是在打他的脸。我看着他,
语气平静。“大公子说的是。只是,这刁奴贪到了我头上,若是我不亲自处置,
怕是镇不住这静安苑的牛鬼蛇神。”我刻意加重了“静安苑”三个字。这是我的地盘。
裴修的眉头皱了起来。“她贪了多少,照价赔偿,赶出府就是。何必动用家法,传出去,
也有损相府颜面。”“颜面?”我笑了,“一个奴才,骑在主子头上作威作福,
这才是没颜面!今天我若是不罚她,往后,这府里的人,是不是都觉得我沈月华好欺负?
”我的声音不大,却字字清晰。“大公子,我知道她是你的人。可如今,她犯了错,就该罚!
”“我今天,还就非罚不可了!”我看向那几个呆若木鸡的管事,声音陡然转厉。“怎么,
我的话,不管用了吗?还是说,在这个家,只有大公子的話,才算话?”这是诛心之言。
把裴修架在了火上烤。他若再保,就是不把我这个主母放在眼里,是僭越。裴修的脸色,
瞬间变得铁青。他死死地盯着我,眼中像是有风暴在酝酿。我们对视着,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
许久,他缓缓开口,声音里像是淬了冰。“夫人说的是。
”他转头对管事说:“按夫人说的办。”说完,他拂袖而去,再没看我一眼。
刘婆子被拖了下去,很快,院外就传来了凄厉的惨叫声。院里的下人们,个个噤若寒蝉,
头埋得低低的。我知道,从今天起,再没人敢小瞧我这个静安苑的女主人。我打的,
是刘婆子。立的,是我沈月华的威。05处置了刘婆子,我在府里的日子清净了许多。
下人们见了我,都恭恭敬敬,不敢有半分怠慢。我知道,他们怕的不是我,是那二十板子,
是裴修的退让。而裴修,自那日后,便再没来过我的院子。我们俩,算是彻底撕破了脸。
我不在乎。我和他之间,本就是你死我活的局面。我所有的精力,都放在了允哥儿身上。
他长得很快,一天一个样。白白胖胖的,见人就笑,特别招人喜欢。裴文远只要得空,
就会来抱他。爷孙俩在一起,总能听到相爷爽朗的笑声。老夫人也几乎天天都来。
她会给允哥儿带各种小玩意儿,金的长命锁,玉的平安扣,堆满了摇篮。
看着这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,我心里却始终绷着一根弦。这府里,太静了。静得让我不安。
裴修不是个肯吃亏的人。他吃了这么大一个暗亏,不可能就这么算了。他在等一个机会。
一个可以把我,连同我的孩子,一起打入深渊的机会。这个机会,很快就来了。
允哥儿半岁的时候,开始出疹子。起初只是几颗红点,府医来看了,说是寻常的奶疹,
开了些药膏。可擦了几天,疹子不仅没退,反而越来越多,连成一片。允哥儿开始发热,
哭闹不休,整夜不睡。我急得嘴上起了燎泡。裴文远请了宫里的太医。太医诊了半天,
眉头紧锁。“夫人,小公子这不是奶疹,倒像是……中了毒。”中毒!这两个字像晴天霹雳,
炸得我头晕目眩。我一把抓住太医的袖子:“太医,你可看清楚了?允哥...他还这么小,
怎么会中毒?”太医叹了口气:“这毒下得极巧,并非剧毒。而是通过母体,
一点点传给小公子的。应当是夫人您,在哺乳期误食了什么相克之物。”通过我?
我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。所有入口的东西,我都用银针试过,怎么还会中毒?
裴文远脸色铁青,立刻下令,彻查我的饮食。很快,结果就出来了。
问题出在我每日喝的燕窝里。燕窝本身没问题。但用来炖燕窝的木炭,有问题。
那是一种叫“乌香木”的炭,燃烧时会产生一种无色无味的毒烟。毒性极微,
成人闻了毫无影响。但若是我这个哺乳的母亲长期吸入,毒素就会通过乳汁,渡给孩子。
久而久之,孩子便会体弱,发疹,高热不退。最终,会像一个正常的病弱孩子一样,
悄无声-息地夭折。好毒的计谋!不伤我分毫,却招招要我儿子的命!我瘫坐在地上,
浑身冰冷。我日日防,夜夜防,防住了入口的食物,却没防住这无孔不入的毒烟。
裴文远勃然大怒,下令封锁全府,彻查乌香木的来源。木炭是厨房统一采买的。负责采买的,
正是接替刘婆子的新管事。而这个管事,是裴修提拔上来的。所有的线索,都指向了裴修。
老夫人得到消息,匆匆赶来。她看到病榻上脸色通红的允哥儿,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
“我的乖孙……”她转头看向裴文远,声音颤抖:“相爷,这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
”裴文远没说话,只是看着门口。裴修来了。他一个人来的,步履从容,
脸上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表情。他走进屋,先是看了看允哥儿,才对裴文远和老夫人行礼。
“祖父,祖母。”“你还有脸叫我祖父!”裴文远把一个茶杯狠狠摔在他脚下,“说!
是不是你做的!”茶杯碎裂,瓷片四溅。裴修却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
“孙儿不知祖父在说什么。”“不知?”裴文远怒极反笑,“采买是你的人,
乌香木经了他的手进了我的相府,毒害了我的嫡子!你跟我说你不知?
”裴修垂下眼帘:“孙儿用人不明,是孙儿的过失。孙儿甘愿受罚。”他认了过失,
却不认罪名。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老夫人也反应过来,连忙上前扶住裴文远。“相爷,
您消消气。修儿的为人您是知道的,他断不会做出此等残害手足的禽兽之事啊!
定是那刁奴自作主张,或是受了外人指使!”她开始为裴修辩解。我知道,
她一定会保她的长孙。我看着他们。看着暴怒的裴文远,哭泣的老夫人,
和那个永远冷静自持的裴修。我的心,一点点沉了下去。这就是裴修的计谋。他算准了,
就算事情败露,也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是他主使。他算准了,老夫人一定会保他。他最多,
也就是一个“用人不明”的过失。而我的允哥儿,却差点丢了性命!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
我扶着桌子,慢慢站起来。我走到裴修面前,抬起手,用尽全身力气,狠狠给了他一个耳光。
“啪”的一声,清脆响亮。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裴修的脸上,迅速浮起五道指印。他看着我,
眼中终于有了一丝裂痕,是震惊,是愤怒,是不可置信。“你……”“我什么?
”我迎着他的目光,一字一句地说,“裴修,你用人不明,害我孩儿性命垂危。
我身为他的母亲,打你一巴掌,过分吗?”我转向老夫人:“母亲,您说,过分吗?